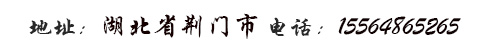南开明史学第期专题研究高艳
|
明代中朝贸易及贸易中的相互了解 高艳林 摘要:明代中朝两国的密切联系,带动了两国贸易上的往来。中国对朝鲜的贸易主要集中于明初的几朝,朝鲜对中国的贸易则贯通有明一代。两国间的贸易,较好地解决了各自所需而本国又不能保证供给的问题,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使两国在贸易中得到了相互了解。 关键词:明朝;朝鲜王朝;使臣;贸易 明代的中朝贸易,传统观点认为,是“朝贡贸易”,即朝鲜国王向中国皇帝贡献物品,中国皇帝再向朝鲜国王回赐物品的物品交换。“朝贡贸易”只是明代中朝贸易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更为大量的贸易形式则表现为双方以各自需要为目的、以货币为媒介的物品买卖,而这种贸易形式,以往研究得还不多,或研究得还不够系统,因此,对于明代中朝贸易的这种形式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笔者拟根据《明实录》、《李朝实录》以及明代朝鲜历史文献等资料探讨此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对朝鲜的贸易 明代中国对朝鲜的贸易有官方贸易和使臣贸易两种形式。官方贸易是指明朝皇帝指令用织物(缎子、绵布、绢等)购买朝鲜马、牛等的一种贸易形式,这种贸易主要集中于洪武、建文、永乐、宣德和景泰几朝;使臣贸易是指中国使臣利用出使朝鲜的机会,带去一些私人物品,在朝鲜交换当地的土特产品,这种贸易因是随使臣出使时进行的,所以明代历朝都有。1.官方贸易明代中国对朝鲜的官方贸易,从商品物种上讲,主要集中于对朝鲜马匹的购买上;从贸易程式上看,则首先是由中国皇帝确定贸易数量及贸易价格,其次是皇帝派遣中国使臣出使朝鲜,向朝鲜国王传达其旨意,再次是由朝鲜方面组织人员将马匹运送辽东,最后是中国将马价运往辽东交割。洪武初年,明朝军队为继续追剿逃往漠北的残元势力,需要马匹。洪武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臣前往高丽,命高丽王朝协助使臣征调前元牧养在耽罗济州的好马两千匹。不料其中多有变故,最后,明朝只得马八百三十七匹。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征马,此后,中国变征马为贸马。洪武十九年(),高丽贺圣节使安翊等由京师回还,太祖皇帝让他们给国王捎话,中国要买马五千匹,并且已将马价——一万匹缎子、四万匹绵布运往了辽东,每匹马缎子二匹。高丽国王给予了配合,不久,五千匹马在洪武二十年的三月至五月,分五批运往辽东。建文三年()九月,建文帝遣使臣陆颙赴朝鲜,传旨国王,中国要换马一万匹,并依照朝鲜的时价交易。对此,朝鲜政府详细地制定了马价:上等马:缎子四匹,或绢十匹;中等马:绢八匹或绵布十二匹。各等马均配给白花蛇、木香、乳香等诸般药材。不久,燕王在“靖难”之役中获胜,建文帝失去皇位,而此次交易尚未完成。虽然中国已换得了七千匹马,但遗在朝鲜的中国马价还有缎子九百二十八匹,绢五千三百八十四匹,绵布三百零八匹。永乐元年()四月,兵部移咨朝鲜,请买完该项马匹,即送辽东都司交割。朝鲜接咨后,于该年六月遣兵曹典书契眉寿押送易换马二千五百四十八匹到辽东。至此,建文时期开始的那次中朝布马交易才告结束。永乐时期是中朝布马(牛)贸易最为活跃的时期,其交易次数之多、交易量之大,远远超过其他各个时期。永乐二年()四月,成祖皇帝遣使臣掌印司卿韩帖木儿等出使朝鲜,购买耕牛万头,以供辽东屯田之用,并定价“每一头绢一匹,布四匹”。同年六月,皇帝命户部将绢一万匹,布四万匹运送辽东,以付其值。至永乐时期,漠北蒙古的前元势力仍虎视中原,骚扰不断,大有向纵深发展、危及北京之势,成祖皇帝决定亲征漠北,扫除这股势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充足的战马支持显得十分重要。永乐七年()十月,成祖皇帝遣内使黄俨赴朝鲜,购买马匹。朝鲜国王根据国内的马匹情况,向中国卖马一万匹。永乐八年()三月,朝鲜将一万匹马分批解运辽东,八月,皇帝命发绢三万匹于辽东,支付马价。此后,为了准备继续亲征漠北,成祖皇帝又分别于十九年()和二十一年(),再向朝鲜买马二万匹。这两次买马的马价是合并在一起支付的。二十一年六月,朝廷内官海寿付奏,给还朝鲜十九年、二十一年两次贸马的马价,每匹该给绢三匹、绵布二匹。户部令辽东可用库存绢布先预付一部分,如有不敷,户部再补运。朝鲜使臣柳衍义等于二十一年十月只领受了十九年马价的一部分(其数无载)。二十二年二月,柳衍义又分两次领受了绢布共八万八千二百九十匹的马价。但中国并未支付完毕这两次贸易的全部马价。宣德二年(),“行在户部奏:‘永乐二十一年敕朝鲜送马二万匹,令辽东都司以官贮大布四万、大绢六万酬其直(值),以布绢不足,困循至今,请领山东布政司运送辽东,如数酬之。’上曰:‘远夷不可失信,复敢稽缓者罪之’”。宣德二年三月,宣宗皇帝遣内官昌盛出使朝鲜,欲向朝鲜买马五千匹,以资边用,并敕曰,马至则酬其直(值)。该年七月,朝鲜方面将五千匹马运往了辽东,但中国支付马价的情况,就笔者所见的史料未载,不过,未付其值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其真实情况如何,存疑待考。据史料粗略统计,明代中朝两国共进行了11次的布马(牛)贸易,中国从朝鲜贸马匹,牛头。中国支付马、牛价:缎子匹,布匹,绢匹,合计匹,此外,还有大量木香、乳香、白花蛇等药材。2.使臣(私人)贸易使臣贸易,其性质属于私人贸易,而非国家行为。此外,并非每一行次的中国使臣在出使朝鲜时都有贸易行为发生。因此,从性质上看,中国的使臣贸易仅是官方贸易的补充形式,在中朝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较小,从史料上看,文官使臣出使朝鲜时,进行贸易活动较少,宦官使臣出使朝鲜时,却多进行贸易。兹举两例:永乐二十一年(),太监海寿等出使朝鲜,“海寿与元闵生(朝鲜官员)言曰:‘予之所赍私物一两日内毕贸易。’海寿出小绢匹,欲换厚纸。礼曹启:‘使臣欲换厚纸,请京中及各道以陈米豆贸易’”。成化十九年(),使臣太监郑同出使朝鲜,郑同语朝鲜馆伴曰:“头目等千山万水辛苦而来者,欲得尺寸之利也。今若所赍之物未毕贩卖,还载而归,则岂非可怜。须以土豹皮、狐皮、胡椒、黄白蜡、山獭皮,人参等物官为贸易。”馆伴以启,国王许之。明代,中国宦官虽多次出使朝鲜,而且有的所行的贸易量也较大,但因中国使臣出使朝鲜的次数不多,所以中国使臣所从事的这种私人贸易的总贸易量,还是不大的,因此,这种贸易不是明代中国对朝鲜的主要贸易形式。二、朝鲜对中国的贸易 明初,太祖和太宗皇帝就制定了明朝向朝鲜开放中国市场的政策。如,永乐二年(),太宗皇帝明确指示辽东:“就著辽东都司于镇辽千户所立市,若那里人(指朝鲜人)要将物货来做买卖的,听从其便。”这表明了明朝实行的是允许朝鲜官、私各方与中国通商,进行贸易的政策,此后的各朝也一直奉行这种政策。但在明代,高丽及后来的朝鲜政府对朝鲜私人与中国进行的贸易采取了完全禁止的政策。一经发现有人越境与中国贸易,重者处以极刑,轻者没收财产,杖配水军。这样,朝鲜私人对中国所进行的贸易被完全禁止,朝鲜对中国的贸易只留下了官方贸易这唯一的渠道。 明代,朝鲜对中国的官方贸易,是由朝鲜使臣完成的。每当使臣出使中国之时,国王和政府责令其完成国家规定的贸易项目,并以法律对其约束:“赴京通事公物不用意贸来者,囚禁推考,以判书有违律论断。”这是一种独特的贸易形式,故此,我们与其说它们是官方贸易,毋宁说是使臣贸易。 朝鲜使臣贸易的内容较为复杂。使臣在出使中国之时,国王和政府委以使臣购买国内没有但又很需要的物品,如药材等,这即是官方贸易,朝鲜政府称之为“官贸”、“公贸”等。后来,使臣也顺便捎些自己的私有物品,在完成国家委以的贸易任务之外,同时将这些私有物品进行贸易,并获得了成功。朝鲜官方把这种贸易称之为“私人贸易”,或简称为“私贸”。为使“官贸”得以顺利进行,国家有限度地承认这种私贸的合法性。由于私贸给使臣带来了意外的利益和收获,于是,使臣在出使中国时,所赍带的私人物品越来越多,其结果,私贸在使臣全部贸易量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此外,中国官方曾规定,凡涉嫌军用物资和中国特有的稀有物品等,严禁外国人在中国进行贸易,如弓角、烟硝、缎面的《史记》、白的青花瓷器皿等等。这其中有些则正是朝鲜极为需要、而本国内又不能生产、完全依赖中国市场供给的重要物品,如弓角、烟硝等。因此,从满足本国需要出发,朝鲜政府不顾中国的禁令,或依仗着与中国较为特殊的关系,默许使臣进行这些物品贸易,朝鲜官方把这种贸易称之为“潜贸”,而中国人称之为“违禁贸易”。朝鲜使臣的每一次贸易活动,同时出现了“公贸”、“私贸”和“违禁贸易”这三种贸易内容的复杂局面。相比较而言,“公贸”和“私贸”基本是同时出现的,而“违禁贸易”出现得较晚,大致在永乐末至宣德初年。而从这三种贸易内容的发展情况来看,明初期,使臣贸易以“公贸”为主,而明中后期,由于白银被大量开采,以及白银在朝鲜与中国的差价较大,给使臣贸易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此,这一时期,“私贸”则成为使臣贸易的主要内容。据笔者统计,在明朝的年中,高丽——朝鲜使臣出使中国共计个行次,平均每年4.6个行次。笔者也考察出,平均每一个行次的使团队伍人数大约在30人左右。这样看来,平均每年约有人次的使臣及其使团队伍成员出使中国,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贸易队伍”。以下,笔者将分别对使臣的各种贸易形式及内容作一简要论述。 1.公贸易(官贸) 公贸易早在洪武初年就已产生了。洪武三年()、四年()中书省臣和户部官员三次向太祖皇帝禀报,高丽使臣入贡者多赍私物货鬻,建议或征其税,或加以禁止。但太祖皇帝三次下诏勿征勿禁。太祖皇帝对高丽使臣的贸易活动一直采取不征税且不限贸易量的态度,奠定了有明一代中国对朝鲜使臣贸易的政策,这种态度和政策为朝鲜对中国贸易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永乐时期,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使臣公贸的品种和数量都有所增加。永乐四年(),朝鲜国王命吏曹自今每当使臣出使中国之时,以医员一人充当打角夫差遣,贸易药材。永乐一朝,朝鲜太宗和世宗国王都把药材贸易作为使臣贸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一再嘱之。大量史料表明,此后的朝鲜历代国王也都将药材贸易定为每一行次使臣必行的公务之一,并有法律规定:“赴京医员通事等所买唐药材不准数者及题名外他药材买来者,启闻科罪,并以本色追征”。永乐十一年(),朝鲜皇亲权永均、任添年等人赴京问皇帝起居,行前,朝鲜国王授与麻布匹、人参斛,以买锦缎。自永乐时期始,朝鲜历代国王朝服以缎料制做,王国内大臣的朝服也逐渐以缎料取代了布料。这样,缎子在使臣贸易总量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以至成为公贸易的主要内容。 弘治时期,是朝鲜废王燕山君(—6)任国王时期,据不完全记载,在他在位的12年里,指令使臣贸易中国货物达21次之多,贸易的物品种类涉及吃、穿、用等几十个品种,其中以缎子居多;贸易数量也相当大,如,弘治十八年(5),国王传:“燕脂一千片,粉一千斤,赴京使臣每一行次都要准数贸来”。至他任国王的第三年头上,用于使臣贸易所耗费的绵布累计已达四万三千余匹之多,按平均每年4.6个使臣行次计算,三年近14个行次,平均每一使臣行次所赍公贸易布匹达三千零七十匹。燕山君于正德元年被废掉,他在位时大量贸易的中国货物,使人们感受到了消费这些物品时所产生的愉悦,这给朝鲜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 使臣公贸易经过多年的发展,至嘉靖年间,已经空前地膨胀起来了,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是:其一,洪武、建文时期的中朝布马贸易,特别是第十代国王燕山君时期大量贸易中国丝织品等所造成的极大的社会影响已不能消除。其二,朝鲜咸境道白银的大量开采和使用更加快速地推动了贸易的发展。嘉靖九年()、二十三年(),朝鲜两遭国丧,使臣素服入朝。虽皇帝赐花不敢插,但彩缎、真珠、圭玉等物则贸易不辍,公贸如旧。国丧期如此,其他行次使臣贸易就可想而知了。 2.私人贸易 私人贸易是伴随着公贸易产生的。这种贸易之所以能够产生,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广阔的国内市场,巨大的利益诱惑。例如,中国特产——缎子,是朝鲜民众最喜爱的物品之一,故而在朝鲜有很好的需求市场。一当有使臣赴京,便有权贵之家愿以多付价钱为条件,求贸绫罗缎子及异物珍货。于是私贸就很容易地产生和扩大了。第二,为满足个人所需。一当使臣赴京,其亲族、士大夫等多有求请之物,另外,使臣个人也会有自己所需购买的物品。所以,情理难却,私贸自然会产生。第三,国内执政官求赂。史料载:“时每奉使人还,执政视赂多少,高下其官。或不如欲,必中伤之。以故奉使者,(为)规免其祸,不得不货市。”任君礼之父任彦忠是汉人,以译官得参朝鲜开国功臣。任君礼也以译官身份屡次出使中国,以致巨富。因此人未给高官以贿赂,便以“为人贪鄙”之罪名,于永乐十九年()被朝鲜政府车裂于市。可见,高官求赂是使臣进行私贸的另一个催生剂。 永乐三年(),鉴于使臣私人贸易数量不断增加,朝鲜王朝立“入朝使臣驮载之法”。议政府议:使臣每一驮不过百斤,除土物外,金银禁物赍持者,论如律。国王从议政府之议。但政府的规定,使臣并不执行。五年(),谢恩使南城君洪恕、书状官金为民、打角夫韩仲老纷纷因私贸获罪。十五年(),使臣都总制李都芳、大司宪李泼等因私贸,皆被罢职。面对不断出现的私贸,国王又采取了疏导的措施,命户曹详定允许赴京使臣私赍布物数量。户曹议:使、副使各十五匹(布),从事官十匹,打角夫五匹。除茶、参外,其余杂物一律禁断。国王应允了这个规定。可以说,这个规定是朝鲜国王、政府对私贸的一种公开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进步意义。 随着政府对私贸的政策有所放宽,私贸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弘治时期,使臣私贸易在贸易商品对象和所持等价物上,均有所变化。在贸易物品对象上,除了纱罗绫缎之外,凡系朝鲜国内获利多的商品,如铅、铁等均纳入了使臣私贸的范围。使臣所赍持等价物,过去以布为主,这时多以它物为主,如胡椒,价值量大,又便于携带,且在中国需求市场亦大,利于贸易,因而使臣多赍持此物。此外使臣也偶赍金银。如金城童在出使中国时,因赍持金银贸易,被处以绞刑。 正德年间,朝鲜咸境道端川银矿被开采,炼银技术也日益成熟,端川的银不但品好,而且出得也多,故而银价甚贱。于是,赴京使臣纷纷弃他物而携银。至嘉靖时期,随着白银被大量地开采出来,私贸易比公贸易以更加强劲的势头发展起来了。十六年(),贺万寿圣节使臣户曹参判赵竖范贸易镴铁至二十余驮。(注:一驮约斤,20驮计斤)回还事发,以辱命毁节,亏损国体下诏狱罪之。这一时期私贸易规模之大,可从宪府以下所言看出:“赴京之行搜银之法不为不严,而奸细之徒,万端生谋,期于必赍,多至万余两,小不下数千两。及其还也,所贸唐物,车辆之数,不可胜计。”由于大量品好的端川银流入中国市场,吊起了中国商人的胃口,以至凡贸易,中国商人皆曰:“非端川银不可。”由此可见,自白银被大量开采出来以后,使臣私贸易无论就其贸易的物品种类,抑或是数量都比以往有了质的变化。 3.违禁贸易 使臣的违禁贸易多集中于弓角和烟硝等物。 宣德九年(),朝鲜国王召大臣议在中国贸易烟硝之事。这一年,国王派遣使臣朴信生赴北京贺千秋节,并顺呈关于贸易火药咨文于礼部。咨文内曰:“本国钦蒙太祖皇帝以‘不分化外,一视同仁’之义,曾于洪武年间,颁降捕倭所用火火通、火药物料。缘本国工匠未识煮取烟硝之法,制造未精,今欲用价收买,未敢擅便,呈禀施行。”这是一份朝鲜力图使在中国购买烟硝合法化的咨文,至于这个咨文中的要求是否能被中国获准,他们是没有把握的,于是,在使臣出发以前,国王召大臣议论此事。国王与大臣做了假设,其一,如果礼部答之“虽不奏达(皇帝),犹可贸易”,则是最好的结果,可除去呈文,直接贸易。其二,如礼部答之“义当奏达”,虽进呈文,但有不肯之色,则不得贸易,这样就得潜贸,且此事宜其谨密,京城内不可潜隐贸易,通州以东(可)潜隐贸易以来。关于此次呈文一事,虽发生在宣德九年,但就朝鲜对潜贸地点、方法的熟知程度推测,违禁贸易应在此之前就早已存在了。 天顺六年(),有使臣从北京回还,向国王报告了女真使臣入中国时因购买水牛角及火药等物,事发被劾之事。这事对国王震动很大,他对大臣们说,以此观之,我国也不能从中国买水牛角了。这条史料反映出,朝鲜一直在关心着从中国潜贸弓角之事。 由于朝鲜的数次奏请,以及在中国的朝鲜籍宦官郑同等人的积极运作推动,成化十三年(),宪宗皇帝允许朝鲜每年在中国收买弓角50副,成化十七年(),又允每年增买副,这样,朝鲜每年可在中国收买弓角总数达副之多。但朝鲜仍嫌不够,使臣的违禁贸易仍在继续进行。成化二十三年(),贺皇太子千秋节使臣柳洵一行在辽东私买弓角事发,都司立案审问。 嘉靖时期,违禁贸易已纳入了国家贸易的计划范围之中,且其方法也与以往有所不同。三十四年(),宪府启:“今者,例贸之外(指年贸对弓角之外),即令暗贸弓角;又使译官行至辽东,托病留住,潜贸铜镴,涉于欺诬。上之事大如是,而何以禁下人之不正乎?请勿暗贸弓角,且勿令译官落后潜贸铜镴。”国王令大臣议此事。领议政府沈连源等议:“弓角贸易,由来已久。前者译官名录差批到辽东,称病留在,有此例矣。”据此议,国王传政院:“令冬至使所带通事贸易。”万历二十年(),爆发了中朝联合抗倭战争,此时,虽明朝已允许朝鲜每年贸烟硝三千斤,但违禁贸易依然严重地存在着,“一行射利之辈到处多贸烟硝,年例则许贸三千斤,而今则例外私贸之数多至累千。通判张文达送其标下搜捉犯禁硝黄而去……已捉之数多至七千四百斤”。 三、中朝在贸易中的相互了解 明代的中朝贸易,不但使两国的各自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而且有利于两国借机加深相互了解。但就中国来看,主动与朝鲜进行贸易的次数较少,了解朝鲜自然资源、物产等情况的积极性不高,对朝鲜的了解具有被动的特点;而朝鲜多主动与中国进行贸易,因此,了解中国情况的积极性很高,具有主动的特点。 明朝以布易换朝鲜马(牛)是这一时期中国主动与朝鲜进行的唯一的贸易形式,这种贸易的进行均与战争的发生有关。当战争平息后,这种贸易即告结束,并未持久地进行下去。并且,即使是这若干次的布马交易,进行得也并非顺利。主要问题是,中国对朝鲜马(牛)市场不作调查,对其情况缺乏了解,交易量的确定是盲目进行的,从而导致交易发生困难。如,建文三年,建文帝打算向朝鲜买马一万匹,而且要求由朝鲜方面确定马价,但因朝鲜供马困难,在很长的时间内只完成了七千匹的交易量。又如,宣德七年,宣宗皇帝敕谕朝鲜国王,中国欲买牛一万头,后又因朝鲜无牛可卖,最后,中国只买到了牛一千头。下面一个典型事例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土木之败后,为备战,景泰皇帝欲从朝鲜购马三万匹,以助军旅之用。但朝鲜根本没有这么多的马匹可以卖给明朝,加之不久后战事稍息,故此次贸易,朝鲜只向中国卖马匹。由于中国对朝鲜市场了解不清,盲目确定交易量,致使朝鲜方面为满足中国的要求,常常以老马、瘦马甚至是幼马充数,从而造成中国或不能全数购买,或购买的马(牛)质量不高。这些情况的出现,究其原因,是明朝皇帝及大臣们的潜意识中,认为中国富有四海,物品应有尽有,无需求助于外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并未打算长期地与朝鲜进行贸易,因而也就不会主动地去了解朝鲜的经济情况,一旦产生与朝鲜交易的需要,就会因情况不了解而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中国对朝鲜了解的被动性特点,除了表现在对朝鲜国内的物产了解不够外,还表现在对朝鲜购买中国物品的迫切愿望了解不够,以致对朝鲜在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同时给辽东人民带来利益上的损害没有足够的准备及应对措施。中国政府对朝鲜使臣在中国进行的贸易采取的不收税、贸易量不限之政策,从客观上,在促使朝鲜对中国贸易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给本已残破的中国驿路带来了更加沉重的负担。由于朝鲜使臣频繁地往返于中朝之间,长期、大量地贸易中国物品,辽东驿路的车夫为了运输这些越来越多的物品,已无力备车,以致发展到了车夫为给朝鲜使臣备车而卖妻儿的地步。实无所措者,自缢而死者也有之。永平府所举行的科举考试,曾给考生出了一道与朝鲜使臣贸易有关的题目,可谓发人深思。该题云:“朝鲜依凭进贡,使命频繁,多行贸易之事,辽东困弊。今若拒绝,则有乖待夷之道,不绝则辽东益困。”朝鲜对中国贸易的快速发展,已极大地损害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辽东地区人民的利益,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个中原因,很大程度是中国对朝鲜贪贸欲望认识不足,了解不够,而又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所造成的。 与明朝对对方不注意了解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朝鲜对中国很注意了解。上文提到的朝鲜对潜贸地点分布的熟知程度,即是一典型事例。他们对中国市场货物的情形也了解得很清楚。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朝鲜使臣经常贸易的货物品种看出。除上文已提到的朝鲜使臣对中国贸易的物品外,据史料载,主要还有以下四大类若干品种:食品类:砂糖、解酒槟榔、各样甘梨、龙眼、荔枝、西瓜、甘瓜、各样水果等;织物类:各样毡绒、各色缎、各色罗、各色纻丝、各色纱等;动物及虫类:马、牝马、牝羊、骡、驴、蝎子等;奢侈品及其他类:玉、白玉、白的青花瓷器、挂香、孔雀羽、貂皮、七宝、大珊瑚、明珀、琥珀、犀角带、三纸、象毛等。朝鲜使臣从中国贸易物品的品种如此之多,显然是建立在非常熟悉中国市场货物品种基础之上的。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交换规律同样非常了解。当时朝鲜使臣根据中国市场的行情,不断调整等价物的形式,凡中国市场需求的物品,都成为使臣赍来中国的等价物形式,如胡椒、把参等。至正德末嘉靖初以后,使臣多赍白银至中国进行贸易,致使贸易进行得更加顺畅。当时朝鲜为什么对中国的经济情况非常了解呢?这当与其经济资源与中国相比相对匮乏、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比相对低下有关。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不得不发展对中国的交流,而交流的前提乃在于了解对方。 其时,在贸易过程中,朝鲜对中国的了解是多方面的,而对中国经济发展、物货富足、人民生活殷实的了解与认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当朝鲜使臣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对中国的富有深感惊叹。有的使臣写道:“余见辽东人民物货之盛,以为更无此比。及至山海关,则辽东真如河伯之秋水,以为天下殷富,此为无敌。今见通州,则山海关又不啻山店贫村,彩胜银幡令人集目。至北京城中,街市则秀堆金窟,左右眩晃。”使臣赵濈也曾在《燕行录》中写到,邹平县虽是山东最为残破的一个县,而物品之丰盛也远胜于朝鲜王京。正是由于朝鲜使臣看到和了解到了中国经济的繁荣、物货的昌盛,才更加激起了他们对中国贸易的积极性。也正因为这些人“平生未尝见一奇货”,所以“一朝入大国金穴,其左右眩乱,无非骇目,惊心之物,其安得不汲汲营营如是”,“一行人眩于买卖,如狂如痴,无一在馆内者,呼之不答,往往多错应”。可以说,朝鲜使臣对中国的这种了解与认识,以及积极主动地与中国进行贸易,无不起到了一种宣传作用,对朝鲜社会认识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朝鲜对中国贸易的不断扩大,大量的中国货物流入了朝鲜,得到了朝鲜上到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喜爱,他们热衷于使用中国物品,已经达到了“服饰竞用唐物,上下无别”,“至于婚可,非异土之物拟不成礼”的地步。因此,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说,朝鲜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与认识是通过使用中国的物品得到的,从这一点上看,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从客观上促使整个朝鲜社会对中国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与认识,加深了对中国的感情,也更加促进了中朝两国之间的密切联系。 文献来源:《求是学刊》5年第4期,第-页。文中注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高艳林,生,天津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廊坊师范学院明史与明代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中朝关系史、明代人口史、天津地方史等。 编辑:宋文 校对:侯振龙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uiniujiaoa.com/snjsltx/4642.html
- 上一篇文章: 陈冠希亲自开撕闪电黑丝绸AF1撕开
- 下一篇文章: 新冠肺炎中医防治综合方案欧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