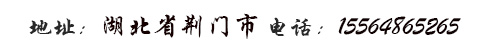一把牛角梳
|
中科大型白癜风公益援助 http://m.39.net/pf/a_6169140.html 一口刚被粉刷过的窑洞里冒出了一串老人痛苦的哀嚎声,呼声此起彼伏。 她瘫在炕上已经不少时日,常年累月的行动不便已经渐渐的使她原本饱满而健康的皮肤干煸,她的白发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她的眼眶也已凹陷下去,她那黄玉般的最后一颗牙齿也在一个月前因为啃半截玉米棒子而拉扯掉了;她的双手变成了僵硬的鸡爪——伸展不开,也握不成拳头;她原本舒展的骨骼也已团缩成弓形状态——那是因为常年保持那个她认为舒服的姿态所导致的;从她的背后能够很清晰的看见一根被黄灿灿的尿液充满的输液管子(顺尿管)。 “人了么?死干心了,把你们这匣(些)龟子孙!” 老人终于忍不住张着那口豁牙漏气的嘴发出了怒吼,她眼角处两道沟壑般的泪痕也被泪水灌满,由于身体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已使她的血液凝固,本就因退化而剩下为少不多的几处感官也已经变得麻木而毫无知觉。 很显然,她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现在她就像大火灼烧过的树木一般,树上的枝蔓已变成灰烬散在了风中,而所有存活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龙王的天雨中;观音菩萨啊,你睁眼看看这个凄惶的老人吧! 阳光在雕割着龙飞凤舞图案打着麻纸的门窗上沉默,回答她的只有那唰唰的风声,住在窑顶的燕子轻快的飞旋在那用稀泥粘成的窝巢下,叽叽喳喳的声音似乎也在悲叹这个不幸的老人。 窑洞内除去老人瘫爬的土炕上脏乱不堪外,其他地方在用白灰打了一层厚厚的腻子下显得敞亮而干净,新沙发,新茶几,新电视,新的双扇门电冰箱,新的全自动洗衣机,新的面柜,新的案板,新的一摆溜(排)八门柜,这些新的家具应该全部都是为婚嫁而添置的,那这些家具为什么会摆在这里呢?难道是她的后人还没等老人咽气就想把她往出撵?这算不算是一种催命的暗示? 圪旦(院子外)外的斜坡地上一片绿意盎然,茂盛的红豆叶子在太阳的焦烤下奄头塌脑的,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枝玉米秸秆仍然坚挺,高国民拿着撅头闷声叹气的把全部力气都使在了脚下的黄土地上,眼睛还时不时的望着土坎下的窑洞,肚里如同被灌进了一口又苦又咸的碱水,不住的腐蚀着他的肠胃,好几次他都想把这口苦水吐出去,可每当婆姨那双恶毒的眼睛盯上他时,他又把那口苦水给咽下去了。 “妈在喊叫了!”高国民猛的扔下了撅头愤怒似的吼叫了一声,这只温厚的老牛竟然也有火气? “我听得到,让她喊么,吼一会就不喊了,咋了,你朝我发火?”白改连慢悠悠的拿起葫芦瓢品了一口苦涩的劣质茶叶水,挑衅似的瞪着高国民。 “我真晓不得你长心着不,对你的老人下亲的见甚给甚,老子的老人就不是人了?差不多就行了!” “哈呀,把你个狗熊,三赖立马就要迎婆姨了,没有一口像样的窑人家鬼跟了,就你是好人么,你甚的心也不操,跟你这来年了,坏人都我做了,有本事在城里给你儿买一套房么,村里的人们说我也就罢了,你还没良心的冲我喊叫,我真是没法活了!” 白改连说嚎就嚎,当下就爬在地上还不忘抓一把黄土朝高国民脸上扬了过去。 满面灰尘的高国民还是软了下来,两只胳膊松松垮垮的挂在肩膀上,刚刚跳跃起的火苗瞬时就被浇灭了。 “好改连了,那毕竟是生我养我的老娘,你这样是让村里人戳我的脊梁骨了么。”高国民丧气的坐在地上掏出了一根纸烟噙在嘴上,一股灰色的浓烟从鼻孔里冒出来散在四周很快就消失在了视线,空气是燥热的,但他的心却凉如暗沟里的一潭死水,一方面是他可亲的老娘,一方面是他用汗血辛苦操持来的穷家薄业,这让他如何抉择,生活就是这样,它时常会把你推向陡峭的悬崖稍有闪失你就可能万劫不复,而现实更是让你不能向自己所期盼的美好的方向所发展,这是一种无可奈何而又无法超越的主观条件,谁都无法改变。 “一年半载的无所谓,她可是瘫了三年啊!久病床下无孝子,咱们够尽心了,三赖的婚房她住着,还要怎么了,她受罪,我们才叫受罪了,活受罪!” “那是让她住么,你是让她死了,光窑里的油漆味和白灰味就能把人呛死,更不用说白天黑夜的不关一下门了,硬硬的把老人的窑霸占了,你不得好死你!”高国民当然不敢这么说,他也只是想想。 妥协有时候并非是自己情愿的堕落,我们可以妥协,但一定要有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与一颗向善弃恶内心! 老人的呻吟声渐渐平息,她费力的抬了下脖子,那把牛角梳还在,它用一根红绳子掉在了对面的挂镜上,门外的风吹了进来,牛角梳如同古老的吊钟一般左右晃动着,在此同时也勾起了老人无尽的思念,而老人的神情也开始变得庄严肃穆。 孩子的世界大多是欢声笑语的,成年人的世界更是充满了无限激情与生活的五味杂全,但老年人的世界却是灰暗且单一的,他们没有了渴望与冲动,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心中勾勒出一副岁月变迁的回忆世界,而且通常这种情感是无比强烈的,因为无人聆听所以就无处发泄,他们是孤独的苦行僧,只等待神明的安慰或者恶鬼的勾魂。 那是一个春天,正值文革前夕,时下社会使得人心惶惶不安,自土改后国家再次进入了一种疯狂而紧张的危机之中,打地主、闹革命、夺政权、评等级、划界限,农业合作化的大风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刮到了那片贫瘠的黄土地上。 刘月英很不幸就成为了那个时代下的牺牲产物,由于她爷爷是地主成分,导致了她无论是生活中还是政治道路上都受人谩骂与摒弃,尤其她还是个很爱美的女孩,她的衣服虽然到处补丁但时常用肥皂洗的干干净净,她的牙齿也用碱面刷的白森森的(那个时候农村人是不刷牙的),更绝的是她在所有的方口布鞋上分别秀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图案,她的总总举动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一种资本主义倾向,她的学习很好,好几年她都达到了省城大学的分数线,但总会因为支书的一句话:“你成分不好就不要跳达,好好的改造,党并没有放弃你,只是你现在还并没有完全融入到咱们社会主义潮流中来,等甚会和咱农民打成一片了再说罢!”而宣告失败。 在那一段时光中,她是极其自卑而又郁闷的,她常常会躲到村后边的土畔上,望着蓝个乍乍的天空,再看看棉絮一样散散零零的白云,她就会想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世界呢?那里会不会也有压迫与无奈呢?从黄昏到日落再到天黑,她能如同雕塑一般的坐在同一地方纹丝不动,有时候她甚至会去数天上的星星,可以想象得到她是多么的无助与寂寞啊,有时候她又会莫名其妙的喊上几嗓子,当然回应她的都是自己重复的声音,她真的好可怜好孤愤啊,所以第二天的时候她就会更加拼命的劳动,人们都说她是个二杆子假小子,她不理会,她已经麻木了,但她会报复似的把肮脏的汗水洒进这给予她无限耻辱的黄土地上,这时候人们又会说这汝子疯了,这辈子也嫁不出去了,生活啊!生活,你究竟要把多少的苦难要降临到这个女人身上啊,她毕竟还很年轻啊,她毕竟还是可爱的啊,她那刚刚丰满的羽翼还未展翅就被无情的社会折断在了起飞的地平线上,这实在是一场劫难。 再后来,刘月英果然没有嫁出去,她今年已经二十七岁了,但还是没有媒人在她家院子里来踩一个脚踪,在农村来说超过二十五岁还未出嫁的汝子是要经受世人的唾骂与嘲笑的,而年迈的父亲也被气的躺在炕上只等着咽气了,但她不在乎,她不怕闲言碎语,唯一觉得对不住的就是把她拉扯大的父亲,可她也无能为力啊,她想:没人要了我就不嫁了,虽然日子过的烂包点,但这是社会形式啊,所有人都穷,因此伺候着老人入土她还是很有自信的,她有手有脚有力气,她不怕吃苦,她读过不少书,所以她知道在山的那边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的道路是水泥柏油路,那里的房子都是高楼大厦,那里的人有文化有知识不会像村里的人一样短浅而偏见,因此她就想着等老人走了就出外边刮去呀,等她发迹了一定要回到这个穷山沟来,让那些曾经打压与嘲笑过她的人看看,我刘月英成分再不好也比你们吃香,当然这也只是她黑间睡下思谋的并不成熟的计划,等太阳出来天明的时候她照旧会去村委会领上一把撅头如同牛一般的耕耘在那片黄土地上,埋没在那黄土乱飞的人潮中,不管她的心情怎样起伏跌宕,黄土大地仍然是那么的沉默与厚实,它不仅能孕育出丰收的粮食同时它还能容纳体谅人类一切的心酸与苦辣。 也许是老天的眷顾,也许是命运的垂怜,终于有人接手了刘月英。 他是一个乞丐,讨吃讨到了刘月英的门跟前,饥饿已经使他忘记了最基本的道谢礼仪,他扢蹴在葡萄架下一口气就吃了四个黑馍馍,直到这时他才抬起头望向了那个使他重新燃起新生希望的救命恩人,呀!原来是个女菩萨啊,他羞愧的老脸一红压着嗓子说了句谢谢,刘月英并没有注意他的紧促,这样的吃相与窘迫当然不会引起刘月英的嘲讽,相反的她同情他,正如同情她自己一样,他的饥饿在肠胃,而她的饥饿却在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精神世界里,温饱固然美好甜蜜,而饥饿落魄却可以激发人类共同合作与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 他不说话,她也不说话,时间在空白中溜走,刘月英终于看清了他的面容,在那肮脏的黑泥下隐藏的却是一张因饥饿而引发的冷峻面容,那如同毡片子般的头发下也同时射发出了太阳般的光芒,现在,那张窜脸胡的面孔正冲着刘月英微笑,好暖心的微笑啊,这应该是近些年来刘月英唯一看到过的真诚的笑容,这笑容如同春风般吹乱了她的春心,是啊,她毕竟还未尝过爱情的果实啊,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总之使她心里毛乍乍的。 短暂的沉默被窑里一阵持久的咳嗽声打破了。 “英子,谁啊?” “啊,过路的。”她实在无法把“讨吃要饭的”这句话说出口,这不光是她刚刚泛起对这位陌生男性异样感觉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从本质意义上来讲她是个善良的人,她深刻的明白尊严对于一个不幸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促使人生存下去的勇气!因而,她完全具备着黄土大地上自古以来就有的那朴实而又单纯的伟大品质。 “哪里的?” 老父亲知道女儿是个好心的汝子,她不愿把他的来路明说,但老父亲也猜出了个大概。 还未等刘月英开口,他就抢先朝窑里喊了一声:“绥德的”。 “好嗓子,常听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后生,你进来一下。” 他腼腆的笑了笑便带着些许的拘谨走进了窑洞,然后他就像做错事的孩子般等待着老父亲的审讯。 “嗯,不错,确实光眉俊眼的。”老父亲像是回光普照一样突然有了精神与体力,他盘腿坐在炕上微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他。 老父亲问:“成家了没?” 他摸了摸后脑勺不好意思的说:“没有,谁家汝子愿意跟咱这吃百家饭的了,被迫的我也习惯了独来独往,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是这,你看我这汝子行不?” 他有些不解但内心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操着一口纯正的陕北口音茫然的说:“好女子,咋?” “今年有多大?” “二十九。” “你属羊,我汝子属鸡,合婚着了,你家里几口人?” “就我一个,本来我们姊妹三个,父亲死的早,母亲前几年因看不起病去世了,而最小的妹子也在黑间被狼叼走了,哥哥在西安,不过我并不知道他在哪搭。” “我看你是个好后生,我喜欢直来直去,我们家是地主成分,因此耽误了英子,二十七了连个撩逗她的人都没有,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就入赘到我这儿,我把汝子交给你,能行?”老父亲扣了下脚片子就等着陕北后生回话。 他呆住了,虽然他刚才思谋到了老父亲的意思,但没想到老人会做出如此草率的决定,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啊,他做梦也怕梦不见这么个好事了,他的心即忐忑又亢奋还带着些许的怯弱,他的心完全乱了。 “爸,你胡说甚了,老傻了吧?”刘月英强忍着内心的悸动带着朴素的矜持笑斥着老父亲,她在刚才又重新观察了一回他,这人身上有股莫名的悍性在不住的吸引着她,即便是跟着他讨吃要饭她也觉得心安的很,她甚至在想他是喜欢小子还是汝子了,以后了又要几个小子几个汝子呢?总之她的心也乱了,好像有只无形的大手从她的全身抚摸过使她融化了,许多年的抑郁与隐忍在这一刻似乎都随着这个人的出现而消失了,她看到的不再是虚幻而毁灭的深渊,而是一种沐浴在阳光下田野里扑鼻的清甜的稻香中。 “能行,我不挑,大呀,我这就给您磕头!” 老父亲笑了,也哭了。 “快起来,现在不兴这一套了,让外人看见影响不好,我是实在惊怕了,原来下我也就不谋活了,可如今我却不想死了,人们以为我刘老汉不行了,让他们看着吧,姓刘的永远是姓刘的!” “哦,对了,这是我妈留下的唯一一件保存完好的东西,虽然我走街串巷的上门讨吃,可这把牛角梳子我却一直带着,妹子你愿意跟我好的话你就收下!” 刘月英当然收下了,她在心里感激他:你若不嫌弃我,我就有信心跟你操持起一个殷实的家庭。就这样,他们结合了,不过他在将来孩子的姓头上与老父亲起了争执,最后在刘月英的协调下做出了一个合理的方案——必须有一个带把的小子姓刘。 刘月英终于结婚了,这一事件在左附临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过当人们知道她是与一个乞丐结合后马上就又有了新的说辞,看吧!原来是地主配乞丐、歪对对歪对——瞎活了么!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见不得别人的幸福,当阳光洒进不幸的人的世界后,他们就会把黑暗以及痛苦强行的带入别人的内心,不过我们就暂且原谅他们的无知吧,至于他们那龌龊的内心迟早总会有硫酸洗涤的。 婚后第一年,他们买了几只猪崽养在了边畔上的烂瓦窑里,他还在院子的葡萄架下搭了一个用葵花杆围起的鸡圈,第二年,他们把窑洞重新刮了一遍,同时他们爱的结晶也降临了,第五年,他们安葬了带着遗憾离开的老父亲,因为刘月英最终也再没养下一男半女,而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也在历史的审判中彻底宣告落幕,至此刘月英的人生也算大踏步的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第六年,由于他的稳重与精干被大队书记选为了村主任,第七年,他们在其他位置重新箍了一口窑洞,据说那块地皮是已故王阴阳反复念叨过的风水宝地。 生活啊,生活,你给他们带来了多少的苦难,你就会还予他们多少的甘甜啊! 牛角梳已经停止,它安静的挂在那里,好似宣告着某种我们所不熟悉的黑洞在渐渐变的明朗,那一道我们永远触摸不到的生命的光辉如同流星般的稍纵即逝,光明与黑暗同时出现又同时消失,眼下白茫一片永无尽头,那欢乐的忧愁的往事如同电影般一幕幕闪过,然后就被毁灭,什么都抓不住了,她的眼神渐渐变得暗淡,但她的意识却异常的清晰,她忘不了他执着的神情,忘不了年轻时黑间睡下他那强健的身体带给她的温存,忘不了他为人处事上恪守的信条,忘不了他愤怒的呐喊,忘不了他生吞下的四个黑馍馍,更忘不了那把他当做信物般的牛角梳。 她原本放不下的儿子与亲疙蛋孙子现在看来也已经放下了,她没有再呼喊,更没有看他们最后一眼的欲望,她的眼泪已经流干。看吧!他回来了,他好像变成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样子,破烂的遮不住肉的衣衫,毛炸炸的窜脸胡,炯炯有神的眼睛,消瘦的面孔,他的笑容还是那么的真诚,他坐在土炕上,他拉起了她的手,然后他们便相跟着走出了不久将用做新房的窑洞,走入另一个世界的美好天堂。 她的灵魂已经飞走了,但她的双眼仍然明灿灿的睁着,牛角梳好像映在了她那双已经毫无色彩的灰暗的眼球上,静静的倒挂着。 天擦黑的时候三赖就下班回来了,他没有回家就跑过来看望他的奶奶,每天都是如此,在他刚开启记忆智灵的那会,他就想着将来一定要好好的孝顺奶奶,果然在他长大后他也是那么做的,奶奶倒下去的时候他很心痛,但同时又无能为力,因此他便养成了一天抽出两个时辰陪奶奶的习惯,他知道母亲对奶奶那种中国式很常见的婆媳间的怨恨,可他又不能对母亲说什么太过火的话,他一直希望父亲会站在他这边而不是盲目的听从于母亲,可父亲却是个怕老婆的赖摆式,因此爷孙三代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微妙而又无奈的状态,三赖无疑也秉承了老人的纯朴与善良,他并没有在母亲的熏染下变得麻木与无情,他能一直保持着自己对于善恶认知的这一品质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总算这个家还有一颗向着光明的心,总算生活的希望并没有完全破灭啊! “奶奶……” 三赖走进窑洞就看见了早已冷透的尸体以及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他的双眼已经噙满泪水,他没有喊叫高国民夫妇,而是自己端了用井水怼上熬水的铜盆子拿手巾开始给老人擦洗身子,当他掀开那面子上看着干净的被套后,刹那间,血液都冲到了他的脑门心! 一股子比尿素化肥更刺激的气味打进了他的鼻孔,护单上黄邋邋的一摊稀屎已经干却,老人的尻蛋子上一片黑青,插输液管子的阴道口子附近也已被漏下的骚尿腐蚀的一片血红,老人腰身以下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了,他忘着挂镜上的牛角梳,似乎也随着它的主人进入了那一片遥远而哀伤的饥渴和洒满幸福岁月的画面中。 无比强烈的痛苦而残忍的愤怒促使他再也忍不住朝着院门外大喊了一声: “人了?把你们这下没良心的龟子孙!” 全书完。 作者简介:姓名:豹豹,柳林成家庄人,普通农民的儿子做着平凡的测量工作,热爱着脚下的黄土大地,以无限激情的劳动来完善自己,人生无外乎就是一场革命,救赎自己不甘于平庸的悸动。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uiniujiaoa.com/snjyfyl/6424.html
- 上一篇文章: 转载我一生积累的19个临床效方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