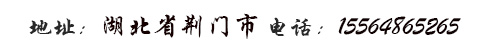红色年代的香格里拉
|
红色年代的香格里拉作者:白郎 历史的甲胄在细节中显形,又在细节中囤积下来。当我怀着缥缈的感叹,从记忆的仓廪中搬出一些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甸(如今叫香格里拉县)的细节时,隐约听到历史的轱辘发出几声既尖锐又祥和的响声,它们像被流水遮隐的藕节子一节节混入苍茫的光影,最终示现为大地的香腮,喂血的刀刃,皓白的云衣,清寂的飘雪,高蹈的鸿鹄,荒废的喇嘛庙,以及大片吟风弄月的青稞...... 在繁忙生活的嘈杂声之上 年代中期,中甸尚处在某种雄阔的苍莽中,境内遍布着鸾峰雪岭,到处是森林。森林帝国的中央是海拔米的县城,它实际上被夹在两排山屏间的草原上,山屏由锥体状的山包连缀而成,每当披满红霞时,它们看上去像是一些巨大的鸟翎。当我到中甸时,县城周围这些山包上翠羽清华的茂林已不复存在,无休止的砍伐使它们变成了荒冷的秃山,只有南面的舞凤山免于浩劫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座两翼高启的凤形青山是当地的神山,残留在人们心头的一点敬畏之情使它得以幸免。 中甸是成立于年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迪庆”的命名者为首任州长、噶丹松赞林寺的大活佛松谋四世。这个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的自治州与西藏相比邻,处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交接地带,除中甸外,还包括维西、德钦二县。 我大概是在迪庆军分区的家属大院里学会说汉话的。这个粉墙乌瓦的大院是个一进两院的院落,位于军分区大门的内侧,我家在进大院后左边的第一家,我父亲时任军分区组织科副科长(他于年乘坐几匹系了红色络缨的高头大马拉着的马车当了兵)。 当时军分区刚成立不久,大门上经常插着几面猩红的红旗,葵花似的骄阳把大片激昂空明的阳光打在上面,使旗子现出富丽的血色,偶尔,有几只大嘴黑羽的乌鸦或晕染着细小黑纹的赤褐色云雀歇在一旁,歇上一阵子,就飞入了青天。大门的入口处终年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不断有穿着圆头大靴或圆头绿胶鞋的军人进出,每个人胸前都佩带着毛主席像章或最时髦的革命小胸章。手臂上套着红卫兵袖套的大孩子们打着口哨在路上乱叫,一些腰杆上插着木头枪的小孩滚着铁环相互追逐,有时候,几个挥舞皮鞭的士兵赶着军马场雄健的军骡匆忙走过,钉着拱形铁掌的骡蹄发出一阵骨头、金属和石头相互撞击时的和声。 (中甸藏公堂) 约翰.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衰落》中说:“在繁忙生活的嘈杂声之上,有一个声音始终不绝于耳,将万物提升到秩序与宁静的境界,这就是钟声。这为人们所熟悉的钟声,像友好的精灵每天伴着人们哀伤,伴着人们高兴,提醒人们注意危险,催促人们虔诚。每个人均熟识钟声的含义,无论敲得如何频繁,人们依然能直觉地反应出各种钟声的意义。”这段话让我回想起军分区每天都会准时发出的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军号声,另一种是《东方红》乐曲,它们均由浑厚的铅灰色大喇叭传出。这两种声音是汇合着政治和军事的经纬之声,它们把生活抓到了一个威严有序的横切面上,并将其洗刷得简单明了。每天黄昏六点,当落日垂下橘红之躯,政治布道歌般的《东方红》乐曲便会响起,它带着无限悦耳的庄重,警示人们一定要忠于中国的救主。 我家边框上涂着绿漆的窗口遥对着青霭四染的舞凤山,不远处的旷野上立着许多栗色青稞架,旷野的西边有一座堡垒似的红土山,上面耸着几株高大的古柏,藏人认为这座山是敬奉护法神的处所,每当遇到病痛灾患时,人们会到山头上的百鸡寺去虔诚地祈祷,并献上一只自家养的放生鸡。文革开始后,这座百鸡翩跹的庙宇便被拆毁了。 由于刚刚学说汉话,还不能很好地和其它孩子交流,我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出现在弥散着淡淡鸡屎味和青草味的大院里,一次,我和大院里的一个小孩发生了冲突,小孩的妈妈把他带走时恶狠狠地骂了我一声“大哑巴”,我母亲知道后,忍不住抱着我痛哭了一场。大院的角落里有一截爬满了绿藓的青石阶,石阶下有个月牙形的小洞,不时有几只全身披戴扁平黑甲的臭甲虫出现在洞口,在藏药的药典里,这种虫可以和紫茉莉、土香等东西调配成医治尿泌病的合剂,我蹲在地上,捉来一只长着复眼和细长触须的大蚂蚁放到虫子中间,想知道臭甲虫是如何围剿蚂蚁的,没想到刚进角斗场,像三个小卵串缀而成的蚂蚁便仓皇逃走了,而虫子们亦有些不屑,它们高傲地站着,懒洋洋地演完了这处《捉放曹》,过了一会儿,我从家里拿来盒火柴,划燃其中的一根去烧臭甲虫,这下一直在玩闲情逸致的虫子们慌了,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后便急忙溜进了洞中。记得有一天,我和妹妹找来些瓦块、芸香草、凤尾蕨及蒲公英在石阶上办姑姑筵,我让她到家里去拿只竹筷,她刚进家门就惨叫着哭喊起来,我跑过去一看,见父亲从乡下买回来的一只雄鸡正抖着大红肉冠跳起来啄她的脸,我奋力赶开雄鸡时,她的脸颊已被啄了一个血孔,我慌忙和闻声赶来的母亲将她带到卫生所去包扎。当天,这只雄鸡便被判处了死刑,吃鸡肉时,我父亲说,只有吃过蜈蚣的鸡才会啄人,这只雄鸡恐怕是吃了蜈蚣才这么凶。从此,妹妹的脸上有了一个笑窝,盈盈一笑间,脉脉送温情,多年后,当她长成丰神秀骨的丽人时,最迷人的地方,却是当年雄鸡为她雕琢的这处笑窝。 分区卫生所在家属大院的北侧,门前种着一大片牛蒡子。牛蒡子是一种清热解毒的中药,别名牛菜,日本人又把它叫做白肌人参,这种草本植物的主根肉质肥大,长着长柄的深绿叶片呈丰硕的牛心状,边缘有波形锯齿,花茎上挂着淡紫的管状花簇,顶端不时吊有一两个长卵形瘦果。在牛蒡子旁的泥路上,我常常会碰到一个年轻的女理发师,姓周,也是从丽江来的纳西人,她留着时尚的齐耳短发,穿着件工作时用的白大褂,纯洁的眸子里满是清愁。不久前,她的未婚夫、一个纳西族军官去世了,这个军官有天去高山上打猎,不小心碰倒了猎人用来对付黑熊的扣子,结果与扣子相连的一排堆有石块的圆木将他压成了肉饼。清旷的阳光把理发师的白大褂照得雪白明晃,几粒反光将她身上的哀思投映到牛蒡子的紫花上,每次遇到我,她都会浅浅地笑笑,然后用纳西话招呼我一下。 (青香树) “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一番深思,终于得以远眺神明的宁静。”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读到瓦雷里的这句诗时,我总会顺着记忆的青藤去眺望迪庆军分区北边的一个湖。这个湖像一只巨大的眼睛,蜿蜒一里的深邃水体宛若青幽的墨玉,中甸人把它称做龙潭。夏秋之际,湖畔盛开着绿绒蒿、马先蒿、银莲、龙胆、点地梅、野百合等野花,芳菲的清气贴着稠衣般的湖面四处流散;柔蔓的水草在浅水里飘拂,一旁立着大丛芦苇,披针形的翠叶间高高挺着花轴上长满了白丝毛的紫色芦花,打着赤脚走进齐腰深的水里,可以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十个脚指头,小虾在双脚间跑来跑去,一群又一群的高山细鳞鱼在风鬟雾鬓的水草中嘻闹。湖水镜子似的倒影着来喝水的牛马、浣衣的藏家女、垂钓的蓑笠翁,以及底翔的鸿雁。如此清凉的净域是自杀者们重要的选择地,文革开始后,几个不堪批斗的人便在这里投湖自尽了。一次,我和几个小孩跟着分区的一个大孩子在湖边玩耍,他用一个石子击中了一只半空中的斑鸠,我们于是点燃一堆火,将这一野味烤熟后瓜分了。不远处,遍野种着青稞、蔓菁和马铃薯,每当收割后,荒凉的田野里会裸露出一些田鼠、土拨鼠的窝,许多肉色的小鼠在里面吱吱直叫,其中有一种遍体无毛的赤鼠,大概由于和刚降生的雏雕长得很像,大雕发现后会把它视作幼子带到巢穴里精心喂养,哪知道赤鼠长大后会乘大雕不备将其咬死,吸食雕血,藏人常以这种鼠来象征负心之人。 湖的北侧是昆明军区独立七营的营地,我父亲曾在这里当过五连的指导员;我对五连的猪圈感到着迷,这里住着一只从山里拣来的小猴,当套着白袖套的猪倌兵把猪群赶到湖畔的草地上去放养时,顽皮的小猴便会在猪身上跳来跳去,要是哪头猪捣蛋掉队了,它就会跑过去狠狠地揪这头猪的耳朵。 年的一大半时间,我和妹妹是在一个墓园斜对面的幼儿园度过的,墓园的铁门涂了绿漆,上方镶刻着一个耀眼的红星,里面是许多烈士的安寝之地,寂静的石墓整齐地掩映在冷翠的青松和幽绿的白桦林中。每个星期五的黄昏,父亲来接我们回家过周末,我母亲在离县城30公里的林业局担任会计,每周末也会回来。幼儿园被紧紧围在由铁灰色柴块排列成的栅栏中,一些朽木幽凉地飘着生前的香气,园门只是一道简陋的柴扉,角落处有一座柴板搭成的厕所,蹲在葫芦形的木板坑上往下扔“炸弹”时,一些夹着黄色碎光的粪水总是被溅出来,所以我每次一扔完“炸弹”,只要听到“呯”的一声,马上就提着裤子迅速往前挪动身位。 (古城老街) 在幼儿园,有许多白昼和许多黑夜,一个脸黑得像砣牛屎的阿姨眯着灵猫似的圆眼教我们唱一首叫《社会主义好》的歌,我记得其中几句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当时,我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类似于大尾巴狼的凶猛动物,很坏很坏。集权时代盛行的一些风气传到了幼儿园,阿姨们要求所有的孩童都必须像小骆驼一样听话,倘若有谁顽皮得过头的话,必将会受到严厉的“镇压”。我记得,最使我惊恐不安的“镇压”措施之一是,当阿姨觉得我不太听话时,会神秘兮兮地用一副危险即将来临的口吻对着我的耳朵说,布谷爷爷就背着大口袋躲在不远处,你不听话的话,他会把你抓进口袋里背走的,到时候我可不管。一听这话,我顿时吓得全身发紧呆若木鸡。由于阿姨们常用这一最有效的招数对付我,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我总是很紧张,我感到自己已处于黑暗的中心,布谷爷爷就在附近游荡,他可怕地微笑着,不停地朝这边张望,背上的大口袋阴森地发出一种棺木松动时的响声,有几次,我甚至在被窝里缩成一团,觉得他就在屋顶上走动,阴黑的瓦块在飕飕夜风中被踩得哗哗直叫。而实际上,我真正见到布谷爷爷已是13岁了,一天,我的同学指着路边一个又矮又瘦的老头说,这个人叫布谷爷爷,我听后吃了一惊,当时,布谷爷爷正以拾穗者的姿势在垃圾堆里悠闲地拣东西,他可笑地穿着一身绿军装,腰间拴着一根花布带,看上去就像是童话里正在劳动的精灵。我的同学告诉我,布谷爷爷和布谷奶奶住在离松赞林寺不远处的一间小木屋里,靠拣拾死猪、死牛、死羊和垃圾为生,尽管膝下无子女,日子过得很苦,倒也其乐融融,有一次,他亲眼看见布谷爷爷背着布谷奶奶赶路,走了一段路后,布谷奶奶又把布谷爷爷背着走,俩人嘻哈打笑,俨然顽童。 在囚笼般的幼儿园,我常常被神秘的黑夜所啄伤,当我在明月下像小豹子一样紧紧抓住木栅栏向外眺望时,感到祖母正挪动着仁慈的身影笑吟吟地朝自己走来,她走得很慢很慢,慢到被遍地月光挡住了来路。淡淡的孤独像斑斓的丝线缠住了幼小的心灵,幼儿园的孩提生活,让我想到里尔克作于年的《豹》: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象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杆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念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年,在常住人口为人的中甸,人们正忙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8月19日,县委作出了《关于“清队”、“一打三反”运动总结报告》,宣布5年来在运动中揭发出有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的人数为人。与此同时,全县掀起了“批林批孔”高潮,县委组织人组成77个巡回辅导组,举办了个培训班,参加人数达人,培训骨干分子人。这股“批林批孔”的劲风也吹到了幼儿园,幼儿园的阿姨在黑板上不断地画出“孔老二”的形象,然后愤怒地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大坏蛋。一连许多天,我和其他幼儿都在阿姨的带领下画孔老二,这是件有趣的事儿,“孔老二”被千篇一律地描绘为--一张大圆脸上,戴着一顶有许多竖纹的瓜皮帽,帽子的中央古怪地耸着一个小圆顶。这种标准像画多了,后来我忍不住在“孔老二”的眼睛上加了副眼镜,再往鼻翼下添了撮电影里日本鬼子最爱留的仁丹胡。一个阿姨看了我画的这种“孔老二”后,伸出大拇指表扬了我一下。 (20世纪70年代的中甸县城) 几朵粘满政治空气的花蕾簇拥着中甸古城 一半是宽大的祥云,一半是衰落的哈达,当文化遭受到大革命,童年生活并未失去那藻饰瑰丽的光影。站在我家门前,能看到一幢雍容的宝殿低垂着迟暮的身相,它是距军分区大门只有数步之遥的藏公堂,藏语叫“独肯端巴夏康”。这幢汇杂着藏汉双重风格的歇山式三层宝殿始建于雍正二年(年),重建于光绪八年(年),它是旧时全城藏民举行集会、议事和佛事的核心场馆。宝殿呈正方形,下层有明廊围廊,上层有圆窗环廊,里面对称排列着38根粗大的方柱;殿顶斗拱垂布檐牙高啄,覆盖着青瓦的屋脊上装饰着宝瓶和伏兽。 我刚到中甸时,藏公堂外常浮游着一股青稞酒醇浓的酒香,酒香是从藏公堂的厢房里传出来的,这里有一个即将被撤销的酒坊,属于军队所有。藏公堂的大殿当时是军队石棉矿的仓库,里面堆放着一些灰白的矿物,几柱清光从木窗里漏进来,使幽暗的大殿显得愈加空寂。文革开始后,狂热的红卫兵冲进了这一中甸古城最为宏大的建筑,他们破坏了大殿下层壁面上崇丽的彩绘壁画及众多文物,但并未实施彻底的暴力狂欢。历史在关键时刻射出了一缕救赎之光——年,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中甸时,藏公堂曾是临时指挥部,总指挥贺龙还在一幅猩红的布幛上写下了“兴盛番族”四个大字。顾忌到这是中甸历史上最“红”的建筑,革命小将们最终在躁动中放下了高举的铁锤和斧头。我隐约记得,光轮像灰鸽的翅膀一样在大殿里暗下来,静默的角落里,竖着一截旧木梯,爬上木梯,可看到大殿上端垂着些破败的五色经幢,斑驳的阴光中,墙面上浮现着美丽的度母、慈祥的坐佛、圣洁的莲花、吉祥的瑞云,当这些神秘的绘像从暗处接连出现时,我不禁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万物高扬着激情。在这红色年代的深处,几朵粘满政治空气的花蕾簇拥着中甸古城。古城的轴心是灵龟似的大龟山,其阳面承接着大自然的阳刚之气,其阴面承接着大自然的阴柔之气,周围环绕着三条老街——北门街,金龙街和仓房街。距藏公堂不足两百米的大龟山是风水中的吉山,山顶的吉壤上,原本耸立着始建于康熙年间(重建于年)的大佛寺,该寺最初得名于一尊丈六金身的释迦牟尼佛像。年文革开始后,珍藏着金汁书写的《甘珠尔》的大佛寺遭到重创,不久,残存的院落被军队的军械所接管,军分区成立后,守护院落的是后勤部的木匠杨坤一家,他的儿子阿幺六是我的伙伴,出于对时势的警觉,出身大户人家的杨师傅对所有人都保持着格外谦恭的微笑。我记得,曼丽的朝阳总是把第一抹香霞投映到大佛寺灰褐色的大门上,天光晴冷,白云广覆,我和阿么六在破败的庙宇前嬉耍,周围飘着一股略微带点檀香味的腐木、青草和泥土的混合气息,几丛墨绿的青蒿里传来甜亮的虫唱,几粒寒鸦浮在半空中,不时撒下两声含着伤逝之情的叫声。 (年的噶丹·松赞林寺) 站在大龟山上能看到古城以北4公里处噶丹松赞林寺庞大的废墟,这座按照布达拉宫形制修造而成的寺庙是滇西北最大的喇嘛寺,始建于五世达赖罗桑嘉措时期,年9月8日至13日,在无与伦比的喧哗中,中甸四清工作团捣毁了这一宗教圣殿,制造了空前的革命“战果”。大龟山东麓的几块灵石下,有一口镶着青石条的敞口老井,水质甘冽,色若玉液,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群前去背水或挑水。背水的多是藏家女,挑水的多是藏家汉,年轻的藏家女往往穿着青蓝色大襟交领长衣,外罩粉红绸缎坎肩,腰系两根红绿绸带,头戴裹有额巾的黑金绒三角帽,发辫上系着红花头绳,中老年藏家女往往身穿氆氇大襟长衣,外罩羊羔皮坎肩,头戴金边帽或盖耳帽,藏家汉子则穿大襟上衣或右衽楚巴,下着布料宽腿裤,小腿上裹有绑腿,头戴护耳皮帽或狐皮帽,脚踏藏靴。藏家汉子喜欢佩戴银质护身符,腰间悬挂黑白牛角刀、德格腰刀和不丹腰刀,有的刀柄上镶有绿松石及珊瑚。这口老井是整个古城惟一的日常水源,专职守井人是一个姓松的藏族大爷,像个高尚的苦行者,他穿着双旧筒靴多年来一直在井旁转来转去,当我和其他小孩拿着井边用桦树皮编成的褐黄色方瓢舀水喝时,他说着有浓厚藏腔的汉话,提醒我们要注意滑倒。20世纪80年代初,松大爷去世了,几年后,千年常清的老井也枯竭了。 “中甸”是一句纳西语,源于明代,意为“酋长住地”(据年版《中甸县志》)。藏族人最早在大唐贞观年间占领了这片“无比殊胜的宝地”,取名为“结塘”,不久,吐蕃在金沙江畔设神川都督府(位于今维西县其宗村),于大龟山建朵克宗寨堡,是为铁桥东城。明朝弘治十二年(年),丽江木氏土司在大龟山建香各瓦寨(藏语意为石山寨,毁于清康熙年间的战乱)。清朝雍正二年(年),副总兵孙宏本率兵进驻中甸,筑土城一座,斜挂于百鸡寺东面山腰,周长丈,高2丈2尺,厚4尺2寸,设有四门城楼,后毁于兵火。民国初年,古城三次被土匪洗掠,县长虞铖于是在年夏天将省府下拔的恤金两以工代赈,动员民众构筑新城。新城在旧城以东,与旧城连环,建有城门四座,城堡8座,周长余丈,高1.2丈,厚6尺,城墙上覆盖着木檐,上面压有草饼,以防风雨。年9月13日,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在此前后,中甸县在古城设立了中心镇。 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几个年头,密布着狂热政治元素的中甸古城尚保持着某种古老的单纯和朴实的明媚,历久不衰的田园生活贯穿了政治硬壳笼盖下的日常细节。类似于中世纪某个城邦的大片民居鳞次栉比,具有藏式雕房与纳西井干式木板房的双重风格;古城与沃野连接处,刺篱形成一排排绿色的帘幕,上面不时浮着一些朦胧的蓝雾。房舍宽大厚拙,多为三楹两层楼房(少数为四楹),底楼作畜厩,楼上住人。楼房三面筑了土墙,前檐呈双层斗拱,中柱普遍在一米以上,需两人合抱,柱顶两端雕有云龙纹饰,下有黑白相间的一截竹篾套,往往插着纸花、麦穗、箭旗、松枝,人字型屋顶内铺垫着小圆木及防腐用的荆棘,上面筑有土掌和木马架,屋顶外覆盖着俗称“闪片”的云杉木片。岁月用一种幽秘的涂料把修长的木片侵蚀成了褐色,常有几只猫在上头自由奔跑,蓝宝石般的眼睛晃动着烈日的强光,有时候,它们对着白云和革命群众发出一阵香艳的叫声,然后像神秘的精灵扬长而去。 (铺有青石板的老街) 铺有青石板的老街上,各种牛、马、猪、羊、狗、鸡和它们的祖先一样,与人平等地在一起来来往往,一些敞养着的牛和猪像无所事事者终日大摇大摆四处闲逛,直到法鼓似的夕阳宣告了白昼即将结束,这些“自然之子”才会惬意地哼着牧歌返回自己的家中。一次,一头高大的牛居然伸出长舌浪漫地舔了我一下。有一天,军分区一个扎着羊角辫的漂亮女孩从一处街头台地往下跳时,不小心跳到了两头猪的背上,猛然受到惊吓的猪尖叫着分头乱窜,撕裂了女孩的下身,医院后缝了很多针。街上到处是牛屎马粪猪尿,没有人会像后来那样大惊小怪地认为这是些不堪入目的秽物,而是更多地将其熟视作草类的另一种固态存在。天高地旷,万类呈祥,一股混合着酥油、牛奶、青稞、青草和动物粪的气味经久弥漫。不少地方庄严地张贴着大字报和革命标语,当严冬到来时,一些饥饿的牛通常会大发反革命脾气,张开阔嘴撕下贴在墙上的各种革命标签,舔食粘在上面的糨糊。我记得,每天黄昏,街上挤满了从外面归来的牛,这个时候上街,往往会落入牛的包围圈之中。列维.斯特劳斯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也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形。中甸的高原牛主要有牦牛、犏牛、黄牛三种,牦牛全身披着长长的密毛,尾蓬如帚,四蹄坚韧钝圆,圆而大的眼睛朝外凸出,母牦牛性情温顺,额头较窄,双角细长优美,公牦牛体态粗犷,性情凶猛好斗,额头要宽得多,弧状的双角威风凛凛地朝前伸着,气力惊人的犏牛是牦牛和黄牛的杂交种,相当高大壮实,两头犏牛拉着古老的二牛抬杠式犁架,每天可平均犁地4亩,若挽拉1.2吨的木料,可日行山路15-20公里。每年的五六月份,藏民都会为牦牛剪上一次毛,牦牛毛粗中夹绒,韧性好,亮度强,是制作毛绳、藏毯、帐篷的上好材料。 藏家女总是在黄昏时分端出奶桶来挤奶,每头乳牛每年可挤出几百公斤的奶,挤奶前,一般先要给乳牛喂些掺了少量青稞面的熟蔓菁、洋芋或青草。我母亲的好朋友莲莲嬢嬢的家在北门街,我不时看见她妈妈在自家的宅院里挤奶,老人家披着宽大的羊皮披肩,手上套着个漂亮的银镯,一道道纯白的牛奶流下来,使一旁的银镯充满了一种香醇的梦幻之美。有的藏家女边挤奶会边唱歌,唱上几句时尚的革命歌曲,再拔高嗓子唱起高旷抒情的藏歌来,两种截然相反的曲调,带着一个时代上下翻飞的灵息,让我多年后想起了尼采所说的:音乐是“反映世间的酒神式镜子”。 古城里很少看到汽车,最高档的车是绿色甲壳虫似的军用吉普,偶尔见军分区的司令坐在里面打着长长的哈欠。当隆重的红色庆典到来时,藏族民兵的马队便会闪亮出场,矮小精悍的马匹多为栗色、骝色及黑色,披着鬃毛的头上往往坠着两条红丝带,马铃声清亮连绵,洋溢着铜质的革命激情,身负长枪的民兵在马背上英姿勃发,大都戴着华丽的狐皮帽,柔艳的狐尾垂在背上,形成了与冰冷的长枪截然相反的妖冶之物。 我不时在一户晒满腌菜的人家前看到一个光着脚丫的孩童,胸前挂着圆盘状的红色毛主席像章,呆呆地坐在阳光里,若有所思。另一些时候,我会在民国时期曾是市场的一片空地上看到一个举着猪尿泡的孩童,灌满了气的猪尿泡比他的头还大,上面布着几道肉色的筋纹,那孩童不停地跑啊跑,那饱含着强劲空灵之气的尿泡,不停地飘啊飘。不远处是一家供销社,几个面红耳赤的酒鬼手持酒瓶站在柜台前,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只鹰在晴空中御风而行,一株香柏在舞落满地圆果,一朵波斯菊在承受绽放之欢,一块玛尼石在清苦地吃着秋色。年秋天,我在藏公堂外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只美丽的彩色蜘蛛,它大概有六、七厘米那么长,身上长着黄、绿、白、黑四种华纹,八条黑白相间的腿像竹节似的动着,它在淡绿色的蛛网上迈着唯美主义的步幅,织出一根根温软的锦线。作为一个派头十足的革命者,鲜艳的彩蛛已张捕到几只飞虫,它怀着一腔绚烂的巫气,似乎在向我宣告:美是残忍之物。 (年代初期,本文作者在中甸) ? 查看作者相关文章请直接点击标题 《少年友人》 欢迎转发、评论,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查看「香格里拉陈俊明」公众平台入驻作者文章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uiniujiaoa.com/snjyfyl/3022.html
- 上一篇文章: FM107提醒这两个感冒药,副作用巨大
- 下一篇文章: 令人费解,一颗60年代的药丸竟然卖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