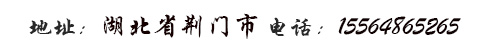韩鼎早期艺术研究中多学科证据的使用
|
北京看白癜风哪里看的好 http://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早期艺术研究中多学科证据的使用问题 韩鼎 (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早期艺术(本文指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因没有同时代相关文献的辅证,使得对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研究者常结合自身知识背景,依据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艺术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材料,对早期艺术进行多角度的探讨。由于多学科的广泛参与,早期艺术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上述学科的相关材料毕竟不是对早期艺术的直接解说,若不考虑证据和被论证对象之间的适用性和契合度问题就主观建构两者间的关联,此类研究的过程和结论往往都不够完善。虽然对几千年前遗物的讨论(尤其是意义方面)不可避免的会有一定的主观性,但至少应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做到尽量客观、规范,以期尽可能排除研究中的主观成分。下文中,笔者将分学科探讨在使用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证据材料探讨早期艺术时容易忽略的问题。 一 考古学角度 考古学为早期艺术品提供了认识基础,如时代、地域、埋藏环境、所属考古学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学科能够进一步研究的前提。我国考古学两个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分别是地层学和类型学,正如张忠培所说:“如果把近代考古比喻为一部车子的话,地层学和类型学则是这车子的两轮。没有车轮,车子是不能向前行驶的;没有地层学和类型学,近代考古学便不能存在,更不能向前发展。”每一位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学者都深谙这两种方法,作为最初的研究者,考古学者在研究中常体现出地层学、类型学方法论的影响。考虑到早期艺术品相对于普通陶器的特殊性,运用地层学、类型学研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01. 地层学 通过叠压、打破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地层学的方法(有时需结合类型学)来判断器物的相对时代关系。但由于艺术品的特殊性,在使用地层学方法判断时代时,应考虑到出土地层的时代与器物制作的时代、地区、所属文化间可能存在的差异问题,这点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认识: 第一,艺术品有更持久的传承性。艺术品常因贵重的材质和精美的造型,历代传承。如经常能在晚期的墓葬中发现早期的艺术品,有时两者间的时代差异甚至可达数千年,墓主人仅是该艺术品的最终收藏者。艺术品出土地层的年代,仅是其可能的最晚制作年代。 如果将艺术品的出土时代直接视为器物的制作年代,并结合该时代的文化背景进行解读,就很容易对其属性、功能、意义发生误判。如我国早期艺术中有一种“神人纹”玉雕(也称“兽面纹”、“神人兽面纹”或“玉人像”),以梭形眼、耳上勾状饰、耳下环状耳饰为主要特征,并多有露出口的上下獠牙。国内外的博物馆中的此类玉雕约有十余件,在未经科学考古出土之前,学界对其时代的看法差异较大,观点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莫衷一是。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在西周时期的丰镐遗址中发现了一件此类玉饰,定名为“玉兽面”(图一:1),各方面特征与馆藏神人纹玉雕均较为一致。因此,学者认为“由于沣西的发现,这类兽面纹玉饰才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考古学的证据。”并依此判断此类神人纹玉雕应属西周时期的艺术品。但八十年代末,在商代的江西新干大墓中出土了一件“神人兽面形玉饰件”(图一:2),又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的肖家屋脊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玉人头像”(图一:3),其主要特征与丰镐遗址出土的玉雕一致。而这两件神人纹玉雕,出土地层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代,地点分别为湖北天门和江西新干,因此,基于西周沣镐遗址出土“玉兽面”而推论此类玉雕皆为西周时期艺术品的判断,就需要反思。三件器物出土地层(所属时代)跨越千余年,地点相距上千公里,由此可见早期艺术品的流传之久、之广。总之,对于艺术品来说,出土地层和制作时代的关系应谨慎判断。 第二,艺术品有更广泛的流通性。艺术品因其珍贵性和稀缺性,在不同文化间交流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陶器等日常用品,战争、贡纳、赏赐、赗赙、婚嫁、收藏等行为都会造成艺术品出土地与制作地之间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差异。 以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器物为例。首先,从出土器物的时代来看:除具有明显商代特征的玉器外,妇好墓还出土有多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多件玉器,如红山文化玉器(图二:1)、石家河文化玉器(图二:2)、山东龙山文化或石峁遗址玉器(图二:3),通过器型的对比我们可大致了解器物的悠久渊源,体现了妇好对古物收藏的热衷。其次,从同时代不同区域的角度来看:妇好墓中出土有若干件北方系青铜刀(图二:4),考虑到甲骨卜辞中对妇好领兵打仗的记载,这些北方系青铜刀很可能是妇好征战的战利品。第三,从妇好墓中的青铜器铭文来看:不同的铭文体现出器物的复杂来源,包括“有武丁赏赐或以武丁为核心的王族成员所作的器物,如‘妇好(好)’器、‘司母辛’器;有妇好生前为他人所作的祭器,如‘司母(司母癸)’器;也有其他贵族进献的器物,如‘亚弜’器、‘亚其’器、‘亚启’器、‘束泉(子束泉)’器、‘’器和‘’器。”通过妇好墓的例子,可以看到同一墓葬出土器物(尤其是早期艺术品)的复杂情形。 02. 类型学 类型学通过研究考古遗存外在形态的分类、变化的逻辑序列,判断遗存的相对年代早晚,建立遗址相对年代序列,确立考古学文化谱系。遗存在同时期内不同形制的差别通常标为“型”,随时间变化产生形制的变化通常标为“式”。宽泛地讲,考古类型学应适用于所有有形之物,如俞伟超曾指出“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研究器物的形态演化规律,人们制造的各种建筑物(包括墓葬)、交通工具、服装,乃至雕塑、书画等物品,都可以用它来研究其形态变化过程。总之,人类制造的物品,只要有一定的形体,都可以用类型学方法来探索其形态变化过程(当然也包括上面的装饰图案);反之,凡是没有形体的东西(如思想、音乐等),就无法用类型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基于这一认识,考古学者在进行器物研究时(包括早期艺术品)往往会以类型学的型式分析作为研究基础,型式分析有助于确定器物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属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认识基础。为更好地将型式分析运用于早期艺术的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视艺术品和陶器的差异。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中,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陶器“数量多,时代和文化特征明显”,“陶器反映年代、地域的变化最为敏感”。因为陶器数量多,所以可以归纳总结其演变规律;又因陶器(和陶器的组合)直接反映了某一人群的生活模式,因此陶器和使用它的人群(及其文化)关联密切;还因为陶器的生产、使用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因此其器型的变化在历时性角度呈现出连续性,这有助于器物的断代。而反观早期艺术,有些情况下仅是零星发现,数量少、分布情况复杂,难以看出连续演变的过程,而且有时器物的纹饰、造型明显表现出与精神领域的紧密关联,再加之艺术创作可能存在的主观能动性等原因,对于这类早期艺术品来说,类型学分析就有些捉襟见肘了。如个别学者主观地(而非归纳)将仅有的几个(难以判断时空关系的)例证,也进行型式分析,有时一件器物即是一“型”,类型学分析所要建构的时代序列、文化谱系均无法实现,似乎是为了型式分析而分析。 其次,对部分早期艺术品的型式分析标准因人而异,造成同一纹饰的类型学体系纷繁复杂。和对待陶器相似,纹饰的类型学分析也常以纹饰内的某一“特征”为分型标准,但该特征的选取却缺乏标准,如对饕餮纹的型式分析,学界总体上有两种分类标准,即按“角”分类和按“身”分类。 按“角”分类的研究:马承源将兽面纹(饕餮纹)分为虎头纹、外卷角、内卷角、曲折角、分枝角、长颈鹿角、牛头纹、变形兽面纹,共八类(图三)。林巳奈夫将之分为无角、T形羊角、羊角、大耳、牛角、几字羽冠、水牛角、茸形耳、尖叶角、羊角形二段角、大眉、两尖大耳、其他,共十三类。江伊莉将之分为虎耳、牛角、羊角、鹿角、麂角,共五类。段勇将之分为牛角类、羊角类、豕耳类、变异类,共四类。 按“身”分类的研究:张光直将饕餮纹分为独立兽头和兽头连身两大类。陈公柔、张长寿则分为独立兽面纹、歧尾兽面纹、连体兽面纹和分解兽面纹四大类。岳洪彬将之分为一首双身、有首无身(或称独立兽面纹)和怪异兽面纹三大类。朱凤瀚则将之分为有首亦有身的不简省类、有首无身的简省类两类,其中不简省类又分为三型,简省类分为两型(图四)。 通过上文中的举例可以看到各家分类方法的差异,因人而异的分类系统势必影响学术交流的深入。因为饕餮纹的多变性,使其在一定的时间范畴内常出现整体形象相近而局部特征(或角、或身)相互置换的情况,如果按此局部特征(如角)作为型式分析的标准,就会造成:除角不同但其他各部分完全一致的饕餮纹被分在不同类中;或仅角相同,但其他各部分完全不同的饕餮纹被分在同类中。如果说型式分析的目的是探索其形态变化过程,确立时间发展序列,那么面对饕餮纹的多变性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功效了。而西方学者罗越用风格学的方法来分析青铜器纹饰(下详),将其划分为五种风格(虽然五种风格说目前看来并不够完善),但其分类模式保证了每类纹饰整体特征的一致性,确有可取之处。细节分析不足是其缺陷,而这正是类型学所擅长的,面对多变的饕餮纹笔者认为可将风格学和类型学结合起来使用,综合发挥各方法优势。 总体看来,通过考古地层学、类型学角度对早期艺术进行的探讨,可以为艺术品提供可靠的时空定位和文化归属,是其他各学科可以继续开展研究的前提。但在研究中不应忽视早期艺术品与一般陶器的差异性。谨慎对待所出地层与器物制作年代、地域、所属文化间的关系,尤其对于首次出土的器物更应谨慎对待。另外,对零星发现、数量少、分布情况复杂、且与精神领域(如信仰、观念)具有明显关联的精心设计的艺术品,应考虑类型学的效力问题。而对于局部特征具有多变性的纹样(如饕餮纹),可尝试将风格学和类型学结合分析,避免按局部特征作为分类标准造成分类系统混乱的情况。 二 古文字学角度 甲骨文中以“形”为构字基础的字所占比例很大,据黄德宽统计:甲骨文中指事字占4.32%,象形字占28.51%,会意字占37.81%,三者加起来超过70%。他指出:甲骨文中,象形是最基础的构形方式;指事字多在象形字的基础上附加标指性符号构成;会意字保存着以形相会的原始性。可以说此三者“反映出汉字形成过程中表意类的构形方式所占有的地位。”另一方面,甲骨文中的部分字形与早期艺术形象相近,又因文字本身就承载着意义,所以不少研究尝试通过甲骨文的字义来诠释与字形相近的纹样。的确,同一物象即使呈现在不同载体之上,或以不同模式表现,形象也自然存在相关性,考虑到甲骨文中字义与字形有时会存在关联,所以,古文字角度可为理解早期艺术形象的意义提供重要的启示。 如李济曾利用甲骨文中呈跪坐姿态的字形来探讨殷墟石雕人像。又如在饕餮纹意义研究方面,伦敦大学的汪涛认为饕餮纹即甲骨文中的字,美国学者江伊莉认为饕餮纹实际上表现的是商王佩戴面具的形象,而甲骨文“”(異)字正表现了商王获得动物力量时“异”化的过程。台湾学者袁德星(楚戈)认为饕餮纹的额间纹饰主要包括型和型,和在甲骨文中常连接牺牲名而表示献祭。李慧萍、贺惠陆认为饕餮纹的雏形为双目纹,也就是甲骨文中的“”字。此处暂不讨论上述结论的可信性,但应看到,通过甲骨文的角度的确扩展了饕餮纹研究的视野。 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注意到目前个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正如刘钊在《谈古文字考释方法》指出的“文字来源于图画,但不等同于图画……把文字当作图画,采用‘看图识字’、‘猜测想象’的手段,将古文字考释引入歧途。”文字考释如果出错,自然也会把基于古文字角度的早期艺术研究引入歧途。如何才能更好的从古文字角度探讨早期艺术呢?笔者认为应该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01. 字形来源的判断 判断古文字中“形”之元素“所象之形”是从古文字角度研究早期艺术的基础,但这一判断不应建立在“看着像”之类的主观辨识上,而是应从字形演变和相关字对比两个方面来考察。从字形演变角度来看:同一文字的字形在不同时期常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对于甲骨文来说,倒书、饰笔、线条化、省略、繁简、相通、讹混、变形、随文改字等构形变化都会对字形造成影响。从相关字对比方面:某一构形要素常出现在不同的文字中,因此要综合对比相关文字来确定此构形要素的意义。上述两个方面要求我们应全面搜集该字演变过程中的各种形态,而不是以某一阶段的字形或某种变体为依据,重视最初未讹变形象,同时还要结合相关文字的对比,避免孤证立论。 以甲骨文“”(且)字为例,郭沫若曾认为“‘且’实牡器之象形”,该说影响很大,不少研究凡涉及早期艺术中的陶祖、石祖时,大多会引此为据。但根据陈剑的研究,从文字历时性的发展角度来看:组肥笔类卜辞(应是在甲骨上刻字的最原始形态)中的“且”字“常写作方形或略带圆弧的近似方形,下端横笔的左右也不出头”如(《合集》0)、(《合集》8),字形表现了“长方形俎面加上界阑之形”,而对于形的且字,陈剑认为“其上端或写作弧形,逐渐变为尖形是文字书写中发生的变化,不能作为解释其所象之物的根据。”再根据相关文字的对比来看:“俎”,在金文中写作(三年壺)、(方鼎),“‘俎’的左旁笔画表示俎足之形,这部分笔画加上表示俎面及其上横格的‘且’形,‘俎’字全形实为俎案侧视与俯视之形的结合。”再如“”、“”及其异体“”,甲骨文中写作(《合集》)、(《合集》),表现为刀在俎侧的形象。 通过陈剑对“且”字字形演变的梳理和对相关文字的比较,我们可以确定“且”最初是对俎面的象形,而非男根,只是文字演变过程中的上端尖化才使它形似,我们不应以后起的某一阶段的字形来推测原型。即使认可“且”的原型就是男根形象,那么、等字多出来的(器物腿足部)和(刀)又该如何解释呢? 02. 形义关系的分析 即使字形与早期艺术中的某些形象确有相似性,但若不加考证的就将字义赋予该艺术形象,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字形对字义的提示是非常有限和微弱的,有大量的文字是不能用这种方法进行考释的。许多初形不明或后代已发生讹变的形体则更不能随便用这种方法加以解释。” 比如,有不少古文字中看似表形的部分,实为表音,如“风”借“凤”之()形,但“凤”仅表音;再如“家”字,最初假借“豭”之初文,后加上意符“宀”构成形声字,即“家”从“豭”之初文得声,后来“豭”讹变为“豕”。如果用声旁视为形旁,再结合字义诠释早期艺术中的凤纹或猪形文物,可能就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 03. 文字与艺术形象的来源辨析 用甲骨文来诠释商代艺术的含义属于同时代资料的互证,若论证的当便会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如果用甲骨文去探讨新石器时代艺术品的意义,就需要考虑到时空的差异、各自来源的复杂性等会影响结论的诸多因素。 如有学者用甲骨文中的字来诠释(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蜷体龙形的原型,认为以红山文化蜷体玉龙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玉龙其原型为蛴螬(金龟子幼虫),也即甲骨文中的。但红山文化(BC-BC)与发现甲骨文的殷商时期(BC-BC)毕竟相距有两三千年,这样的时空差异让我们不得不更谨慎地看待两者的联系。笔者认为,将红山文化的蜷体玉龙置于其所属文化的相关器物链中应会得到更加可靠的推测。 在红山文化中,蜷体玉龙的整体特征表现为兽首(包括由哑铃状轮廓线包围的圆形双目、褶皱的吻部,巨大的上竖双耳)和C形“身躯”的组合(图五:1)。但通过与相关器物的对比可知,红山文化蜷体玉龙的兽首和躯体并非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兽首可以单独出现(图五:4)、可以两个结合(图五:5)、可以平面化后单独出现(图五:6)、也可以将吻部变成喙而形成鸮首(图五:7);C形“身躯”也可以和其他动物头部结合,如蜷体玉鸟(图五:2);C形“身躯”也可以独立存在(图五:3)。上述变化主要基于“打破-重组”的构成模式,因此,蜷体玉龙并不是对现实动物的再现,兽首、C形“身躯”都是可以单独出现并相互组合的,蜷体玉龙、蜷体玉鸟就分别是兽首、鸟首与C形“身躯”的组合。如果此推论正确,那么用甲骨文中的字来诠释红山玉龙的原型就可能存在问题。至于“身躯”为何呈C形(或玦状),考虑到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一定程度上的源流关系,笔者认为应与兴隆洼文化的最重要玉器——玉玦有关(此文不再展开)。甲骨文中的确有可能是对蛴螬或类似生物的刻画,源于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而商代的蜷体玉龙则传承于新石器时代的造型传统,文字和文物虽然形似却有不同的来源。因此,在用甲骨文字形诠释早期艺术形象时不应忽视各自形象的来源问题。 三 历史学角度 从历史学角度研究早期艺术,主要途径是用后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诠释考古资料的意义。笔者曾专文讨论过早期艺术研究中的文献使用问题和考古资料的解读问题,这里就不再展开,下面仅简单列举主要观点。 01. 文献使用问题概述 由于与早期艺术相关的文献,在时代(与研究对象时代差异大)、性质(引述和托古混杂)、内容(零散出现、相互抵牾、记载模糊)等方面的情况都较为复杂,因此,用后世文献辅证早期艺术时应更为谨慎,否则,就容易在以下几个方面出现问题:第一,对所引文献缺少在“语境”中的系统认识。脱离语境去理解文献,很容易造成望文生义的情况,同时,也应结合“语境”对文献创作“目的性”进行分析。第二,文献与文物论证关系倒置。应以文物自身呈现的证据链为依据,而不该去挑选考古材料来迎合后世文献的记载。第三,应客观对待文献和文物的“模糊性”对结论的影响,不应“利用”这种“模糊性”使二者对应。 02. “二重证据法”的再思考 很多学者将后世文献来和考古资料(包括早期艺术)结合讨论的模式视为王国维所提的“二重证据法”,但其实两者间有着重要的差异。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何为王国维所提的“二重证据法”进行分析。 在概念方面,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有此种材料,吾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在实践方面,王国维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甲骨文、金文、简帛等)相结合,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按照研究内容、所用证据、相关论著三个方面,我们可将王国维基于“二重证据法”的一系列研究可用下表呈现: 通过“概念”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确定王国维所提“二重证据法”中的“二重证据”指的并非是“传世文献”和“出土器物”。 所谓“二”,指的是“传世文献”(纸上之材料)和“出土文献”(地下之新材料)。这点可以通过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研究中所使用的证据来确定,其中“地下之新材料”指的是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 所谓“重”,指的是“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发生交集、产生关联并可以互证的那部分。两者一致时,相互证明,以证史实;不一致时,证明传世文献之讹误(如王国维通过甲骨卜辞发现了传世文献中商王世系的讹误)。因此,“重”强调了两类证据间的内在关联,这种联系是两类文字材料自身所呈现的,而非人为赋予的。 通过上述简要的分析,我们看到王国维所提出、运用的“二重证据法”是通过强调“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间的内在关联作为研究基础,探讨的是出土文献所属时代的相关历史,取得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如果将“二重证据法”改造为“传世文献”和“出土器物”间的关联,但“出土器物”不会“说话”,所以替它发声的只能是研究者,因此,此“二重证据”间的关联性便不再是自明的,而是由研究者赋予的。而早期艺术品又常体现出神秘性与超自然性,这就使得对它的阐释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同样的纹饰,不同的理解就可以结合不同的文献;而同一文献有时又被用于诠释不同的纹饰。因此,两者间的关联性整体来说较为主观。 那应如何处理“文献”与“考古资料”间的关联呢?笔者认为罗泰提出的“分行合击”很有启示意义,他认为考古材料和文献是两套非常不一样的资料,各有研究方法。过早地把不同的资料混合在一起会影响对遗存、遗迹属性的判断。应在“考古材料”和“文献”的研究各自做到合适的地步以后再结合起来考虑,结果会更加可靠,也更加有意义。这样既能利用文献和考古学整合的优势,又避免考古材料跟着文献走的弊病。 四 文化人类学角度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并对不同人类群体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做出解释。基于这一目标,文化人类学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曾先后出现过诸多理论,尝试从普世角度探讨文化的特征,如进化论、传播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新进化论、象征主义、符号论等等。有学者将这些理论融入我国早期文明和艺术的研究之中,增添了不少新的角度和思路,取得了颇多有洞见的新观点。但个别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01. 忽视理论的发展 随着认识地深入,文化人类学的很多理论和观点在不断被修正、甚至被替代。纵观文化人类学各种理论的发展史,呈现出连续且动态的发展过程,许多新的理论都是基于之前理论的不足应运而生的。因此,在使用某一理论时应充分了解与之有关的学术批评和后起理论对它的补充和修正,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审核该理论,规避已被后续理论指出的弊端和不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个别研究中全盘以某一理论为指导思想,不经审核地接受全部观点,并打破我国早期文明自身的发展脉络,或器物所在的证据链,挑选例子来迎合理论,这种本末关系倒置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对于部分跨学科的研究来说,个别非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学者在借用该学科相关理论时,对该理论的认识与其发展脱节,很多在西方人类学界已被系统反思的理论,不少国内学者对它的认识仍处于其最初传入中国时的水平,如图腾理论。因此,在借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时,应重视理论的发展,避免用已经被修正的理论做“无用功”。 02. 西方理论的契合性 每个文明都有其特殊性,正如博厄斯所说:“只有在每种文化自身的基础上深入每种文化,深入每个民族的思想,并把在人类各个部分发现的文化价值列入我们总的客观研究的范围,客观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这也是博厄斯倡导“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的根源所在。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有它的独特之处,如张光直曾说“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具有普遍的应用性。我们将中国的型态叫做‘连续性’的型态,而将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型态。”当然,很多人类学理论并非基于西方文明所提出,但经过西方人类学家的“目光”,很多理论不自觉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理论和考古资料若能契合,则可以相互发明;若不契合,这也许正体现了中国早期文明的特殊性,是对既有理论体系的补充,正如张光直所说“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根据这些历史事实建立的法则,其适用性会大大加强。”因此,筛选中国的考古资料来迎合西方理论,这种削足适履的研究模式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个别学者们在运用西方人类学理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时,也存在选择的情况,如只选择理论中的某一部分,忽视可能不契合的部分。在评论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类学知识论的变化时,王铭铭认为,变化背后“其始终追求的目标只局限于本文化的自我意识和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支持。”这种态度上的倾向性其实是值得所有人文学科所反思的。 03. 图案和族群的关系 有些研究中,通过人类学理论(如图腾理论)将纹饰图案与族群相关联,用人群关系的变化解释纹饰的变化,也用纹饰变化解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不可否认,新石器时代各区域文明间存在交流,如李新伟就曾对新石器时代晚期不同区域玉器造型及纹饰相似性进行过讨论,认为这种交流仅集中于社会上层,是社会上层获得知识或珍贵物品的途径,用以彰显权利和身份,而就整体文化(族群)而言,仍遵循自身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再如上文所讨论的,早期艺术品有广泛的流通。因此,从个别图案或器型的相似性就推测整个族群间的互动则是有风险的。 还有学者将纹饰图案与族群信仰对象相关联,从信仰融合的角度分析复合型图案。如杨晓能在分析青铜器纹饰含义时,认为“青铜器纹饰实际上是‘泛神动物’崇拜的概括式图像化。它将各种远古始祖、守护神灵、民间群体的膜拜对象、自然神祇,即整个社会的宗教信仰集大成进而赋予具体的视觉形体。”“早期青铜时代的王朝一并承认和分享那些曾经是诸族保护神或族源神的动物神祇的做法,对于完成宗教信仰和礼仪祭祀的整合以及树立王朝的权威显然是成功的。”该理论认为因为青铜器纹饰集合了各族群的神灵,各族群因能从青铜器纹饰的“泛神动物”中找到本族群崇拜物的影子,所以不会排斥它,对纹饰的认同变相的也是对新政权的认同。因而青铜器纹饰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以“同化”异族。这一研究结论颇有启发意义,但却难以解释为何早期饕餮纹非常抽象,没有任何具体动物形象(动物形象的融入均是后起的),在早商阶段抽象的青铜器纹饰中无法找到支持该说的证据。 04. “图腾”泛滥的反思 “图腾”(Totem)源自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原始社会中,人们以某种自然物的图形作为本氏族的保护神和标志,称为图腾。”这一认识也代表了我国大部分学者对“图腾”的看法。我国早期艺术的研究中,“图腾”基本贯穿了所有的讨论,似有滥用的情况。这一现状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反思,如张光直、裴玄德、常金仓、曲枫、施爱东等学者均有过讨论,但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下面笔者结合上述三个方面,简单谈一下我国早期艺术研究中“图腾”理论的使用问题。 第一,从学术史来看,国内学界对“图腾”的认识并没有和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同步。正如《宗教人类学导论》一书中阐述的:“尽管许多人类学的领军人物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uiniujiaoa.com/snjyfyl/7482.html
- 上一篇文章: NewPhytologist胡萝卜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