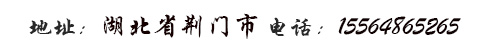散文王德兰牛儿哞哞叫
|
” 王德兰,女,汉族,70后,凤凰办事处教师,喜欢徒步,爱孩子,爱生活,享受在路上的感觉。有文字散见《昭通文学》《昭通作家》《昭通日报》《乌蒙山》《杏坛文苑》。 ” 牛儿哞哞叫 王德兰 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陆陆续续在全国各地农村展开,农民耐以生存的土地从合作社划分到农户家庭个体,极大地刺激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一九八二年,我们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包产到户,生产队的牛、马、羊也随之分到每家每户。我们家分到一头黄牛,俗话说,牛肠马肚,牛儿得吃草,放牛就成了家里的一件大事情。爸爸妈妈要种田地,只得把牛儿关在牛圈,喂些干草,早晚牵牛儿出来饮一次水。牛儿看着满眼的绿草,哞哞地抗议,回到牛圈就懒洋洋地拈几根干草活命,有时候牛儿还会趁饮水的机会挣脱绳子,奔上山坡,狂啃青草。 假期一到,哥哥姐姐就要帮着家里给洋芋薅草,给苞谷追肥。放牛的活儿轻巧一点,自然是十岁的我干了,于是我就成了山坡上的小牧童。我只要把牛儿赶出村子,远离庄稼地,赶到离家很远的山坡上去吃草就行了,到了山坡上,便可以任凭牛儿满山跑,只要它不脱离我的视线范围,我就可以一整天在山坡上玩耍。但是离开爸爸妈妈,我一个人在孤寂的山坡上一整天看着牛儿,听不见一个人的声音,看不见一个人的影子,我害怕极了。那些“老变婆”故事,“黑白无常”的故事总是在我小脑袋里跳跃。整个山上只有呼呼的山风和阵阵隆隆的松涛陪伴着我。晚上,我眼泪汪汪地请求妈妈,我能不能拉着牛儿在妈妈种地的庄稼地边放? 当然不行,庄稼地边的草被薅干净了,牛儿吃不饱,就会糟蹋庄稼,我牵得了牛儿的嘴,牵不住牛儿的四只脚,牛儿踩到自己家的庄稼自己就挨饿,踩到别人家的庄稼,就得赔偿人家。庄稼这东西,几十滴汗水,才换得一颗苞谷,几十滴汗水才换得一颗谷子,糟蹋了庄稼会遭到雷劈的。那时的孩子,字典里没有“不”字,家长负责安排任务,孩子负责执行。第一天放牛回来,我被吓得在睡梦中大喊“老变婆来了!”第二天,妈妈喊八岁的三妹和我一起去放牛,互相做伴,为了鼓励我和三妹安安心心放牛,妈妈每天煮六个洋芋给我和三妹做晌午当奖励。要知道,八二年土地刚刚包产到户,很多人家吃饱饭都是问题,吃晌午可算是奢侈的享受哦。就这样,我俩姐妹每天用小提箩提着洋芋,再用瓜叶包一坨酱,开开心心去放牛了。我和三妹一前一后,三妹牵着拴牛的绳子,我一手提着我们的晌午,一手拿着一根细长细长的竹棍当鞭子,牛儿要吃路边的苞谷,我立即“嗷”地吆喝一声,再把鞭子一甩,细长的竹棍“撕”的一声响,牛儿就住了嘴乖乖地走路了。叔叔婶婶都夸我两姐妹赶牛认真,牛儿走过的地边一株苞谷也不会被糟蹋。不像别家孩子赶牛,只管玩,任凭牛儿边走边糟蹋苞谷。到了山坡上,我们就把绳子解开,牛儿就尽情地啃青草,我和三妹就抓石子宝玩。偶尔抬头看看,如果牛儿走远了,我又大喊一声“嘞”,牛儿便会乖乖转头吃草。当太阳偏西,我们的影子长一点,我和三妹就吃晌午啦!这时,牛儿吃饱了青草,悠闲地站着倒嚼,或者甩甩尾巴驱赶牛背上的蚊蝇。看着我和三妹吃洋芋,牛儿就会摇摇头甩甩耳朵,看着远处的山坡仰头哞哞地高歌几声。我就吆喝牛儿:“贱畜牲,不要偷懒,赶快吃草,晚上回去慢慢倒嚼嘛。”再捡一个小石头扔向牛儿,有时打在牛背上,有时打在牛脚上,我和三妹力气小,打不疼牛儿,只是提醒它继续吃草,牛儿似乎听懂了我们的话,又埋头“嚓、嚓、嚓”地啃青草了。看着牛儿天天吃饱青草,喝饱山泉水,一天天长得膘肥体壮,毛色亮堂。我两姐妹可高兴了。傍晚,太阳躲山凹的时候,鸟儿归林了、虫儿归洞了、蚂蚁归穴了,我们也撵着牛儿回家了。回家的路上,牛儿的肚子吃得鼓鼓的,走路都走不动,路边的苞谷苗牛儿连看都不看一眼,这时就不用拴绳子拉着牛儿了,它会自己回到牛圈里去。叔叔婶婶们见了直夸我们:“你两姊妹放牛真放得好,你看牛儿的两个气塘都吃得撑平啦!” 记得有一天中午,阳光明媚,晴空万里。牛儿正埋头啃青草,我和三妹刚刚吃完洋芋开始玩过家家,对面山上的张大爷爷放的大黄牯牛哞哞地叫了几声,我家的牛儿听见了也哞哞哞地应了几声,然后我家牛儿甩甩尾巴,摇摇头,后脚蹬几下草地,接着撒开四蹄朝着对面山坡狂奔而去。牛儿跑了,跑太快了,一溜烟,三跨两步就下到沟底,张大爷爷家的牛儿也朝我家的牛儿飞奔而来。牛儿要打架啦!张大爷爷家的大黄牯牛可是出了名的凶狠啊,每次牯牛打架都是大赢家。我和三妹吓哭了,追着牛儿边跑边哭边喊:“妈妈,快点,牛儿打架去啦!”隔着几匹山坡薅草的爸妈根本听不见我两姊妹的呼救声,张大爷爷听见了就大声喊:“小姑娘,不要怕,牛儿不会打架的,我在这边看着,你两姊妹慢慢下山了,小心摔着。”我和三妹跑下山坡,远远看见两头牛儿果然没有打架,不仅不打架,两头牛在沟底欢快地哞哞哞地叫一阵,然后互相舔身上的毛,从头上舔到背上,再舔到腰上,又舔腿上,一遍一遍舔遍全身,舔一会儿又互相把身子贴在一起磨蹭……张大爷爷悠闲地把兰花烟裹好插在烟杆里点燃,两个牛儿就在沟底吃草,时而奔跑,时而摇头,时而甩尾。我和三妹看着洋芋地埂上好大一株栽秧果树,又红又大颗的栽秧果吸引了我,我就带三妹去摘栽秧果了。 从那之后,每天张大爷爷撵牛经过我家门前的大路,他家黄牛就哞哞哞地叫,我家的牛儿也在圈里哞哞哞地应,我和三妹就马上提了晌午,牵了牛儿去放。要是哪天我们出来慢一点,张大爷爷家黄牛就一直站在路边不走,哞哞哞地叫唤,直到看见我家牛儿出了院子才昂头挺胸走前面,一路撒欢直奔山坡。 张大爷爷七十多岁,身体硬朗,精瘦精瘦的,穿一件蓝色长衫,腰间系一条白布腰带,腰带是张大爷爷的老母亲过世系的孝系腰带,系了三年,习惯了,一解下腰带就觉得冷,好像少穿一件衣服似的也就一直系着。腰带上插一根两尺多长的烟杆,烟杆是磨得光滑铮亮的竹棍,一端头包了铜皮嘴,一端斗上一个粗粗的铜烟嘴,怀里揣一个牛皮烟盒。烟盒圆圆的,用木漆漆得亮堂堂的,照得出人影,烟盒里面整整齐齐摆放一撮切成寸把长的兰花烟叶子。 张大爷爷要吃烟的时候,他就从怀里掏出烟盒,轻轻拧开,先拿一片烟叶子含在嘴边,不能沾到口水,但是要借助嘴里的热气把烟叶熏软一点,抻平,再拿出几片干脆的烟叶,然后用抻平那片烟叶子做包皮,把干脆的烟叶裹严实,就像现在擀面条的师傅包面一样。这样就裹好一支烟了,裹好的烟插在铜皮烟嘴里,张大爷爷最后再从怀里掏出一封火柴,轻轻推一下火柴盒,捻一根火柴划燃,张大爷爷一边用火柴点烟,一边用嘴呼呼地吸烟杆。当我们看着火柴燃尽的时候,张大爷爷的烟也烧着了,丝丝缕缕的烟圈儿就从张大爷爷的嘴巴和鼻孔飘出来,从嘴里飘出来的烟圈圆形的,一圈一圈的,从鼻孔飘出来的烟子长长的,最后才变成一个小圈。 张大爷爷没有妻儿老小,生产队分牛的时候,那头凶猛的大黄牯牛谁也驯服不了,没有人家敢要,张大爷爷原来在生产队就是放牛的,所以要走了大黄牯牛。村里的爷爷奶奶都说,张大爷爷是国民党的老兵,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在战场上受了伤,自己拖了尸体把自己掩盖着,晚上爬出来,躲到村子里,给老百姓要了一身衣服穿着,后来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张大爷爷一路辗转乞讨回到家乡来,父老乡亲善良厚道,谁也不说这事。何况张大爷爷是打过鬼子的人,相亲们都很尊重他。 张大爷爷亲切、和蔼、爱讲故事。整个生产队有小孩子放牲口的人家,小孩子都喜欢跟着张大爷爷一起上山,有放牛的、有放马的、有放羊的、还有放老母猪的,大大小小五、六个孩子。家长们都请张大爷爷帮忙照看着点,既是照看着牲口也要照看着孩子,张大爷爷喜欢热闹,喜欢一群孩子叽叽喳喳和他说话,每天张大爷爷都乐呵呵地领着孩子们上山去放牧。五、六个孩子跟着张大爷爷放牲口,只有我和三妹提着洋芋去做晌午,我把洋芋一人分一个吃,人人吃得舔嘴抹舌的。张大爷爷就从洋芋地里刨些洋芋,带着大伙儿捡一堆干柴烧洋芋给我们吃。香喷喷,黄爽爽的烧洋芋啊,我们吃得饱饱的,剥洋芋的手一抹满脸的汗水,人人成了小花猫。晚上回家,妈妈问我:“山上的火烟咋个回事?”我就说“张大爷爷带着大伙儿起火烧洋芋吃晌午呢。”爸爸说:“那么大一群人,哪家的洋芋摊上,估计要一大撮箕才够吧。这可不行,时间长了,人家种洋芋的人家吃啥?”爸爸妈妈就不准我和三妹在山上烧洋芋吃,妈妈仍然煮几个洋芋装在小提箩里,我提着去吃。张大爷爷笑着说:“不碍事,不碍事,“放牛娃娃光咚咚,家家地头三升种。” 整个暑假,我们一群小娃娃跟着张大爷爷放牲口,妈妈天天给我和三妹煮洋芋,但是我们两姐妹馋山火烧的洋芋,看着张大爷爷和其他小娃娃呼哧呼哧地吃黄爽爽的烧洋芋,我们直咽口水,张大爷爷就喊我把煮洋芋放火子上烤了分大家吃,这样我和三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吃烧洋芋啦。妈妈放了盐煮的洋芋,经火子慢慢烤热,烤得金黄金黄的,外酥里面,比现在的油糕都香,小伙伴们也争着吃。 每天在山上起火烧晌午成了我们最幸福的时光,洋芋成熟了烧洋芋,苞谷米绽了就掰苞谷棒子来烧,烧苞谷不能把苞谷阔叶全部撕完,要留两张苞谷阔叶包着,放在子门火上慢悠悠地翻烤,待烤熟了,就把苞谷阔叶撕去,露出晶莹剔透的玉米粒,一排排排列着,清香甜糯,每个小娃娃都要啃两大个烧苞谷。毛豆角饱胀了我们就烧毛豆角,烧毛豆角要焖烧,摘一捧毛豆角,刨开火子,放进毛豆,再用棒棒拢一些火子盖上,慢火慢焖,听到呲溜呲溜的声音时,毛豆就面了。张大爷爷就用木棒把毛豆扒出来,我们几个小娃娃就争先恐后地去抓毛豆,张大爷爷就喊:“慢点儿,小心烫手!”山里娃娃皮糟肉厚,我们抓了毛豆马上剥开扔嘴里,甜蜜蜜香喷喷面嘟嘟的毛豆米伴随着我们嘻嘻哈哈的欢笑声在山坡上滚动。瓜儿大了我们就摘一个来烧,烧瓜儿要用瓜叶包好,仍然放子门火里面慢慢焖烧,虽然烧瓜儿比家里的煮瓜儿甜得多,但是烧瓜儿费时费力,要很多火,所以我们只是偶尔烧一次。有时候还烧茄子,烧辣子,烧蚂蚱,烧知了。烧洋芋烧苞谷把我们的肚儿撑得圆滚滚的,火也快灭了,我们几个女孩子就玩老鹰捉小鸡。张大爷爷就带男孩子们去草地上逮蚂蚱,他们折一根树枝,偷偷靠近蚂蚱,用树枝猛一抽打,蚂蚱被他们打残了,他们就捡起青草蚂蚱,不大一会儿,他们就能逮十几只肥嘟嘟的青草蚂蚱,扯一根百花草拴成一大串提回来,像威武的将军凯旋归来。他们把肉唧唧的青草蚂蚱丢火子上,滋,滋,滋,蚂蚱被烧得流油,一会儿就烧死了,再烤一会儿就刨出来,双手把蚂蚱一扯两截,再把蚂蚱的内脏扔了,我们看着那一坨一坨焦黄焦黄的烤蚂蚱肉,抵挡不住香味窜到我们的鼻子,我们猛咽口水。他们问我们要不要,我们咽着口水说不要,他们就一包嘴吃了。其实,不是我不要,而是我看着那一只只青草蚂蚱,瞪着鼓鼓的眼睛,在火堆里挣扎,实在害怕,总觉得那眼神会索命。我就一直强忍口水,不吃蚂蚱肉。张大爷爷确说,知了的肉更香!逮知了很难,必须一个人悄然无声地在树下屏息凝视,瞅准时机,左手一把捂住,慢慢收拢手指,右手小心捏住,迅速扯了知了的翅膀。谁逮到一只知了,一群男孩子们就欢呼雀跃地回到火堆边,把知了直接放小火子上烤脆,然后扯去知了头,分着吃,三四个男娃娃分吃一只知了,每人一丝丝,竟然吃得唇齿弥香。吃完又欢呼雀跃着去逮下一只知了。 张大爷爷种很少的地,没有妻儿拖带,一个人开支也少,夏天以放牛为主,大黄牯牛被他放养得膘肥体壮,冬天就去帮没有牛的乡亲耕地,也不收酬劳,只要管他两顿饭就行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管哪家请他,他都热情答应,饭菜好不好他从不计较,但是,晚上一定要撮一大碗苞谷喂大黄牯牛才行。张大爷爷说:“犁地累,耙田累,加碗牛料牛不累;拉车苦,驮马苦,添升马料不怕苦”。俗话说得好:“使牛要知道牛辛苦!要想马儿跑得好,要给马儿吃得饱。” 冬天的太阳暖暖的,懒洋洋地爬上山头,张大爷爷又领着一群孩子把牲口撵到山沟里去晒太阳。牛儿,马儿都乖乖地站在沟边的沙滩上,悠然自得地享受阳光空气,时而饮一口山泉水,时而啃啃地埂上的草根。只有羊儿站不住,非得满山遍野地跑,小小的嘴搜寻着草根草芽和一切没来得及落光的叶子。放羊的那个孩子就只好跟着羊儿满山遍野地跑,我们几个小伙伴为了玩耍,就帮她把羊儿围在一起,让羊儿和牛儿马儿站在沙滩上。羊儿没草根草芽可啃,就在沙滩上打起架来。羊儿打架非常有趣,我们就尽力促成羊儿打架。不管是绵羊还是山羊,都只有公羊才打架。 不过小绵羊就是小绵羊,一般不太打架。不像牛打头,一战就是你死我活的,牛打头也是只在牯牛之间才有战争发生。在牛界,战争也是让女牛走开。两头牯牛若是干起仗来,那场面及其暴力,及其血腥,及其吓人。牛儿如果不是自己打够了,人力休想分开它们。 我曾亲眼目睹过一次牛打架,两头牯子在距离十米开外的地方同时站定,同时低头,几乎把嘴处到地面,牛角朝前,同时鼓起鸡蛋一样的眼球,四只眼睛同时射出一束束愤怒的凶光,四个鼻孔同时呼出一团团仇恨的气焰,两个嘴巴同时发出沉重的喘息,喘息的气流把地面的尘土沙粒碎石都吹了飞起来,这头牛狠踢一下地面,那头牛也跟着狠踢地面;这头牛发出低沉的怒吼,那头牛也随之发出低沉的怒吼……两头牛就这样对峙着,谁也不敢冒然进攻,一直对峙十几分钟,甚至二十多分钟,双方都觉得自己把握时机了。咣!一声闷响,两头牯牛又是同时前蹄离地,后蹄腾空而起,一跃而上,咣!再一声闷响,两头牯牛的头就撞上了,瞬间牛角绞灼,他们拼力闯,狠劲顶,玩命抵,用力甩、扭、别、杠、撬……不大一会儿,汗水从牛的背上和脖子上渗出来,两头牯牛都像从水里拉出来一样湿淋淋的,但是这畜牲俩就是停不下来,依旧不断地闯、顶、抵、甩、扭、别、杠、撬……直打到牛儿头上,脖子上,前膀上剐出大大小小的血口子,鲜血顺着眼睛皮上和耳朵背后流下来,滴到地上。从牛嘴巴到牛耳朵到牛头顶到牛脖子到牛前膀都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特别是脖子和前膀,找不出巴掌宽的皮是没有受伤的,牛儿也累得精疲力竭,这时身强力壮的两个男子各自拿一根扁担,轻轻拍打一下牛前蹄,并大声呵斥:“贱畜牲,还没打够,要打死啊!”打架的牛就顺势转身离开。历时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一场战争结束,两败俱伤,没有赢家,地面上留下一个深陷的大坑默默地诉说着被践踏的疼痛。张大爷爷当时也在场,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骂骂咧咧地说:“这滚岩的畜牲,挨千刀的,剐牛皮的哟,这回你爷仔受活啦,这回舒泰啦,这一架打下来,二十天都恢复不了。” 在生产队的时候,放牛的人都尽量把牯牛分开放,不让牛界战争发生,若一个生产队有两头好战的牯牛,那必须得分开关在不同的牛圈里,分别由两个饲养员分开放,饲养员约定,早上出门时也要一前一后,前一头牛撵出去,间隔半把个小时左右,再放另一头牛出来。前一头牛放东面坡,后一头就放西面坡;前一头放南边山,后一头就走北边山;晚上收牲口也要一前一后回去。但凡上点岁数的饲养员都心疼牲口,一般不会让牛打头,只有少数年轻后生放牛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意无意让牛儿相遇一起,纵容牛打架发生。后生们像斗鸡似的,都认为自己放的牛身强力壮,想一战成名,牛打赢了比人打赢了都值得炫耀。现在牛儿被分养到每家每户,更是要小心警惕牛打架。牛儿大概自己也明白自己的牛脾气,在山坡上一般不会打架,场地不允许,一旦打架,就会有牛摔下山坡而死,打出牛命来,惨烈得很。大部分牛战都是发生在河坝,沙滩或者其他宽敞的坪子地。听爸爸说,有一年两头水牯子在田里顶起来,因水田里淤泥松软,水牛角又弯成弧形,牛头抵上就没法分开,牛角绞缠脱不开,水牛身体本就笨重,越用力越深陷泥潭,一个生产队的二三十个壮汉分成两组,分别用皮条绳子拴了牛后蹄,拼尽全力拉也没有成功,妇女们心疼得掉眼泪,上年纪的老奶奶们双手合十,不停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牛魔王菩萨快快显灵吧!”最后竟然两头水牛累极而亡,场面血腥、惨烈,牛架史上之最。我们有时候看见有的牛儿只有一只角,有的一只角断了一截,那都是战争中受的伤。我还听见张大爷爷和我爸说(小孩子不敢插嘴,只敢偷听),他年轻时候放牛,有一次牛打头打得厉害了隔不开,张大爷爷说这畜牲也是日怪得很,他就牵一头沙子(母牛)去打架的牛眼前晃悠一圈,牛儿马上就停止打架了。真是牛唉!张大爷爷还说,两头牯牛一辈子只打一架,不论输赢,第二次再遇到就不会打架了,此牛再不理彼牛。还真有牛性!如果牛的力量悬殊过大,也打不起来,他们远远地对峙一阵,力量弱一点的牛会瞅准时机,转身就逃。从此,两头牛一旦相遇,力弱的牛儿就像避瘟神一样躲着力强的牛。 张大爷爷还知道另一个劝牛架的办法。就是当两头牛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用火把去烧牛的嘴和耳朵,也能迅速把牛分开。但是,此法一般没人敢用,听说怒火中烧的牛正在酣战,突然被火把分开了,他们马上迁怒于持火把的人,转而攻击持火把的人,非把持火把的人挑伤不可。 比起恐怖血腥的牛打架,羊儿打架就有趣多了。小绵羊真不喜欢打架,我们把羊群围在河滩头,挑出两只壮实的公羊来,六个小娃娃分成两组,两人推着羊屁股跑,一人在前面伸手指引着羊儿的眼神跑,两组人和羊都同时相向而行,跑到一起了,喊一声“打”。两只羊才半推半就地用头“咚”地撞一下,也不激烈,像两个拳头撞一起一样,接着两只羊踏着小碎步同时小跑后退,退到十多米左右,两羊再同时相向跑来,“咚”撞一下,再退!再跑,再撞!我们有时和羊儿一起跑,有时候大喊加油,但是羊儿最多打四五个回合就再没斗志了,最好玩的是,两只羊儿相向而行,因为羊儿眼睛偏朝两侧,平时看正前方得稍稍偏一下头或者转一下脖子,也很方便,但是集中精力直线前行的时候,羊儿就来不及转一下头看前方,这样一来,两只羊儿相向跑来,就会撞空了,两只羊儿就懵懵懂懂地看一下对方,重新退回去再跑,或者干脆不打了。任凭你怎么诱导羊儿都无动于衷。山羊打架也是撞头,但是,山羊的进攻方式更有趣,两只山羊要打架的时候,他们会站在平一点的地方,面对面站得很近,接着咩咩咩地叫两声,然后两只羊同时扬起前蹄,身子往上跳起,一同落下的同时用头使劲撞对方,撞完再咩咩咩叫,再起跳,再撞!山羊打架也是意思意思一下,最多也是只打四五个回合就偃旗息鼓了,又各自咩咩咩去啃草了。 冬天的河沟边沙滩暖暖的,牲口们悠闲自在地晒太阳。昼短夜长,我也不用带煮洋芋当晌午,地里粮食颗粒归仓,张大爷爷也弄不到洋芋烧晌午,他就给我们讲故事,啥都讲,二郎神的故事,吕洞宾的故事,何仙姑的故事,观世音菩萨的故事,孙悟空的故事,朱元璋放牛的故事,宋江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等等,天上人间,从古至今,什么故事张大爷爷都能讲。 山上的青草绿了又枯,牛儿和我们一起长大。我家的牛儿生了一个小牯牛。我们可高兴了,再养两年,小牯牛就可以耕地啦。爸爸妈妈就不用在数九寒天挖地了。每年冬天,妈妈没有手套,在凛冽的寒风中挖地,挖田,在刺骨的河水里洗衣服,整个冬天,妈妈的手上都布满裂口子,我常常看见血珠珠从妈妈手指上冒出来。我就特别盼望牛儿快快长大。一般情况牛儿长到两岁就可以教了。爸爸妈妈说牛儿辛苦,教小了挣痨啦,一直把牛儿养到三岁才教。 教牛那天早上,爸爸撮一大碗包谷喂了小黄牯牛,小黄牯牛呱嚓呱嚓地咀嚼包谷,爸爸自言自语地说“吃吧吃吧,吃了这一碗你要好好苦啦,下辈子就别做牛了。”待牛儿吃完苞谷,爸爸把它撵到一片开阔的慌地去,我和三妹好奇地跟着去看。只见爸爸在牛肩膀上套上牛耕索,拴上牛打脚,牛打脚后面不拴犁头,而是拴一大截圆木头,刚刚被束缚的小黄牯牛新奇又兴奋,拖着木头疯跑,上窜下跳的,爸爸也不理它,只管自己抽山烟,抽完两杆山烟,小黄牯牛大概跑累了,慢慢地走起来,爸爸就起身把“牛挽手”甩得呼呼作响,大声喊小牯牛“跟沟,跟沟,畜牲跟沟。”爸爸吆喝牛儿,不许走错一步,一定要沿着一条“犁沟”来回往返,也不知道走了几十几百回,牛儿渐渐地不敢越“雷池”一步,一听到“跟沟”,就乖乖走了。说也奇怪,就这样来来回回跑一条“犁沟”,跑了一早上。爸爸说:“好了”。 下午,爸爸就撵上牛儿,扛着犁头去刚刚收割完苞谷草的一块空地里犁地了。来到空地,爸爸喊“站”,牛儿就乖乖站住了。爸爸接着把牛耕索套在牛肩膀上,拴好牛打脚,牛打脚距离犁头还有两尺多远,爸又扶着牛儿肩膀喊一声“缩”,牛儿又乖乖后退两步,刚刚好。最后再把牛打脚套稳犁头,只见爸爸双手熟练地把犁头扶正,再用力踩一下“铧口”,“铧口”就插入泥土,犁头就站稳了,爸爸就用一只手扬起“牛挽手”,一只手扶着犁头把,大喊一声“走,跟沟”。太奇怪啦,牛儿竟然乖乖地朝前挣,“铧口”深深地插入土里,板结的土地瞬间刷刷地翻起一排排土块,牛儿在前,人在后,走到地边边,爸又大喝一声“哇,嘞,嘞嘞”,牛儿就转身往回走,爸爸就顺势把犁头连提带拖跟着牛儿转一百八十度,再次把“铧口”插入泥土,刚刚收割完苞谷的土地,泥土被翻耕出来,新鲜的土块偶尔有肥嘟嘟的土蚕,胖乎乎的蚯蚓也被翻出来,花喜鹊就“佳,佳,佳”地飞来拣食土蚕和蚯蚓。爸扶着犁把,来来回回,一会儿功夫,一大片地就被耕完了。如果人工挖,怎么说也得一个星期吧。 老百姓日出而作,秋收冬藏。在暖暖的阳光里,耕完地的牲口又悠然自得地聚集在沟边河坝晒晒太阳,喝喝山泉。我们几个小娃娃又再次聚拢在一起听张大爷爷讲故事。傍晚收牲口的时候,我们把牛粪,马粪拣拾起来,用背篓背回家积攒着,种苞谷种洋芋的时候做底肥。每一个农村娃都不怕脏,每一个农村娃都勤劳。 冬去春来,夏日炎炎,牛粪拣不起来。妈妈觉得女孩子不能专门学“打山”,得学学“针线”。妈妈扯一块白布,教我“挑花”,先挑简单的围腰带,妈妈教我:“横三纱,直三纱,斜三纱”。妈边说边挑几针,我看了也照着挑,很快我就学会了“挑花”。为妈妈“挑”围腰带,为妹妹们“挑”虎头兜兜,“挑”荷叶边兜兜,“挑”古锁兜兜。奶奶看我小小年纪学会“挑花”,又教我绣花,抛花,做花鞋垫。婶婶,婶娘们都夸我心灵手巧,我也迷上了针线活儿。妈妈给我一绺五彩缤纷的丝线,一块白布,两三天我就在白布上“挑”出活灵活现的牡丹,绣出栩栩如生的蝴蝶。我还跟着姐姐学会了缝衣服,结纽扣,拿鞋底。 我对针线的迷恋,使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天大的错误,至今无法释怀。记得那年夏天,十二岁的我,照例趁暑假去放牛,照例拿着一块白布去绣花。我把牛儿撵到山坡上,就任凭牛儿自己去吃草,我在一棵大树下面坐定,就开始绣花。我绣得非常投入,不知过了多久,我猛一抬头,一头刚出生四十天的小牛犊因为没人提醒,走到了悬崖边上,悬崖边青草茂盛,小畜生不顾一切去够草,我大声呵斥“嘞,嘞”。小畜生被一大簇青草诱惑,对我的呵斥充耳不闻,继续往前够。“咣当”!小牛犊摔下山崖了!“哞哞哞”小牛犊发出凄厉的叫喊声,我疯了似的跑下去救牛儿,岩又高又陡,我根本过不去。小牛儿摔了卡在一条岩缝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明显看出前脚折断了一只,鲜血淋漓。小牛儿痛得“哞哞哞”地惨叫。老母牛听见小牛儿的惨叫声,就奔过来,看着牛儿受伤,老母牛“哞!哞!”地呼唤,大黄牛也飞奔过来,看着妹妹受伤,“哞!哞!”地嚎叫,一时之间,三头牛的“哞!哞”声交汇在山谷里,凄厉,撕心裂肺。我哭着跑到另一块地喊爸爸妈妈来救牛儿,爸爸妈妈扔下锄头,拿起扁担就跟着我跑,他们想把牛儿抬回去。无奈,牛儿摔得实在太重了,头部伤势严重,已经死了。山谷里只剩老母牛和大黄牛“哞哞”地哀嚎,我看见老母牛的眼泪吧嗒吧嗒滴下来,两头牛就这样歇斯底里地看着再也不会“哞哞”的小牛儿哀嚎,怎么赶也赶不走。妈妈回去拿来锄头和三份纸钱,妈妈边烧纸钱边喊“转人生,转人身!”烧完纸钱,爸爸把小牛儿的尸体就地掩埋了。我和爸爸妈妈含泪赶着老母牛和大黄牛回家,老母牛一步三回头,“哞哞”的叫声沙哑,似哀嚎,似低吟,似哭诉…… 第二天放牛,妈妈喊我,别去小牛儿摔岩那个山坡,免得老母牛想起它的儿,再伤心。可是,老母牛一出门就朝着昨天那个山坡狂奔,一直跑到掩埋小牛儿的地方,朝着山沟“哞哞”地哀嚎,叫着叫着,眼泪又掉下来了。每天都要惨叫几个小时,才勉强扯几嘴青草活命,不到一个星期,老母牛迅速消瘦下去。我心怀愧疚,总觉得小牛儿摔死是因为我放牛不专心惹的祸。妈妈说:“怨不得人,牛马牲口命在天不在人。小牛儿早死早超生。”可怜的老母牛痛失小牛儿,白天不吃草,晚上常常仰天长鸣,“哞,哞,哞”的哀嚎刺破静寂的夜空,传到我的耳朵里,击打着我幼小的心脏。老母牛很快就瘦得皮包骨头了。 为了赎罪,我拼命割草,晚上尽量给老母牛加一些夜草,爸爸又给瘦骨嶙峋的老母牛添一碗苞谷面。经过精心调养,老母牛总算渐渐有了膘气。第二年夏天,小牛儿小小的坟萤早已青草茂盛,老母牛路过坟萤时也不再哞哞叫唤了。突然有一天,老母牛又生下一个小牯牛,我又听见了久违的欢快的“哞哞”声。 长相忆,最忆是童年。 长相忆,最忆牛儿哞哞声。 昭通作家 第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uiniujiaoa.com/snjsltx/7521.html
- 上一篇文章: 蒙药特色产品红花清肝十三味丸
- 下一篇文章: 中药循环再记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