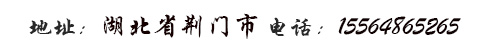静静的菜子河
|
在海南省的琼中县与万宁市、琼海市的交界处是一望无垠的热带森林。山的这边,在琼中县境内有一个叫坡头的管区(现在是和平镇)。一条蜿蜒的小河把这个管区分成两个部分:黎族村和苗族金第们村。在苗族金第们村,有一户最早迁来的蒋姓人家,这个家族族长名叫蒋福,他原先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伙夫。渐渐地,他有了一点积蓄。眼看年纪也不小了,他也有了要结婚的念头。不久,他用五个光银从黎族地主手里买来了蒋氏女子,蒋氏长着张圆圆的脸,尖尖的下巴和长长的耳垂,非常勤劳能干。她家原来在中平镇,中平惨案时,她家恰巧住在山寮,种植些山栏,也是因此逃过一劫,但后来还是被虏掠而去变卖为奴。 蒋福夫妇异常能干,组建家庭不久,家庭就有了八头牛和一些田地,并且生了五男两女7个儿女,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平淡地过着。不久,时代变迁的浪潮和运动席卷而来,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也被卷了进去。蒋福作为村里的长老,更是首当其冲,以身为范。他牵着他那八头牛,纂着田契加入了生产队。白天他卷起裤角和大伙犁田耙田,太阳晒得他的脸成了古铜色。但工分还是不够多,孩子们经常吃不饱。太阳渐渐西沉,乡间渐渐漆黑一片,偶有一两盏煤油灯和闪闪的萤火虫儿,一亮一亮地镶嵌在漆黑中。刹时,漆黑笼罩中也热闹了起来。其它生灵的世界此时已降临。 看着美丽的妻子、可爱的小孩,他拿起了把猎枪,手提着一个手电筒朝着山上走去。一个小时后,他走到一棵牛奶树底下,忽听到树上有“嚓叭”的声音。手电光照过去,一个绿光闪闪。他立刻扶起枪,枪托顶在右胸上,顺着手电光瞄准着那绿光处,右手食指扣下板机,“砰”的一声,一个大物冲撞着牛奶树的枝叶,噼哩叭啦地掉在地上,是一只瓜子狸,足足有九斤重。蒋福急忙走过去,右手提起猎物,左手扛着枪,朝着流水声的方向走去。没多久,他来到了小溪边。溪水哗哗地流着,三三两两的青蛙涌动着白色的肚皮“咯咯”地叫,忽然一只黑影飞疾地越过小溪流,惊得鱼儿也冲进石洞里,水底留下了一条浑浊的长线。不一会熊熊的烈火燃了起来,猎物那绒绒的细毛在火中渐渐消融。很快地,蒋福剥好了果子狸的皮,用粽子叶包好,系上绳子,放进背篓准备背回家。但是猎物的毛焦味随着冰冷的山风吹到村书记那涵洞般黑森森的鼻孔中,一阵寒风吹来,身体不禁颤了一下。一队人马冲了上来把蒋福按在水中,不断地呼喊着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 不久后的一天,半山腰上那白布似的云雾尚未散尽,人们已聚集在生产队的晒谷场上,他牵回了全部八头牛,并全部分给了他的7个子女。之后,他咯出了一口血,没过多久就死去了。俗话说“树大分枝,人大分家”:大女儿嫁去了大陆长沙一位姓李的乡下人;二女儿嫁给烟园村一位姓刘的乡下人。老四入赘到烟园村一户姓盘的人家,其它四个儿子也在村里娶妻生子自立门户。大儿子蒋名从原自治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学校就在河对面的黎族村里,建在村头的山顶上,后面是农场的橡胶园。每天,蒋名都要穿过一片田地,涉河来到学校。路上不时遇到赶早忙农活的乡下人,这时,蒋名通常是微笑着等对方打招呼,然后就用挟杂着汉语的语言回应,经常使那些老农摸不着头脑。“有学问的人都是讲汉语的人”他常常这样想。学校虽地处偏僻,但仍有一些外省人来落户和教书,可能物以稀为贵,汉族人郑肿刚才刚一转正就当上了副校长。 郑肿刚他常把头发梳得油亮,攥着手走来走去。阳光毒辣辣地照着,海南一向如此。球场上有三三两的学生在投球。砰,一个球落在郑肿刚左脚板上。“妈的”,郑肿刚狠狠地骂了一声,接着右脚一抬,把球踢到旁边的水沟里,球不停地水里打转,转得水四处飞溅,形成了一个喷井。“嘎”,一辆摩托车在他前面三米处的槟榔树底下停下。一位名叫王开文的老师朝他走了过来,“校长好”他毕恭毕敬地说。接着递给他一个信封,上面赫然写着琼中教科局一类的字。郑肿刚叼着烟,接过来撕开一看,原来是今年的一级职称指标,名额有五个。他急忙一把塞进口袋里。“是什么东东,搞得这么神密”,王开文问。“没什么”,郑肿刚回答道。接着快步走回了宿舍。 第二天一早,他手里抓着张纸从后门走进了教室里。这时,蒋名正在绘声绘色地站在讲台前上《鸟的乐园》一课,学生们在底下叽叽咕咕着,一见郑肿刚立刻静了下来,如同烧红的铁块投进入水里一般。他刚坐定,蒋名就走到了他身边,“校长”,蒋名低低着声音问候道。“老师,填这张表”,一张表递到了蒋名面前,是一张评课表。蒋名顺手从胸前的口袋里抓出一支笔,凡是标优的全都打了勾,并在评语里写着:“该课基本目标落实……”就递给了郑肿刚。 “今年我们学校有一级职称指标吗”?“没有”,郑肿刚冷冷地答道,迈开大步朝门外走去。“妈呀”,一位女老师发出尖锐的叫声。郑肿刚走得过于冲忙,差点撞上了正来查班的梁玉荣老师的身上。这是一个戴着眼镜,挺丰满的女孩子,高耸的胸部,圆圆如波罗密般的臀时常像磁铁般吸引着男老师的目光。 在橡胶树吐着血红的嫩芽时,学校的布告牌上也焕然一新。一群男女老师们伸长着脖子如同屠夫手提着鸭的脖子一样,不停地发出嘘嘘的声音。原来是郑肿刚通过了一级教师职称的资格审定,正在公示。“为了评职称,我可是连连八年去海口说课,可一直都说没指标。”梁玉荣喃喃地说。“前几天听说我们学校有五个一级职称指标,可我们却不知道”,蒋名说道。太阳更加地猛辣,抱怨声也终于停止了。人们一溜烟地钻进了各自的房间里,拿出彩票图,用笔不停地在上面划呀划呀,数字也愈加神秘,难于预测。一条道路笔直了过来,金光灿灿,蒋名走了过去取走了十万。他在课桌子上不停地摆弄着各种式样的方阵。他对一个矩形图极其满意,就对一个外号叫“光头”的包工头说,“你能照我的图建造出一栋房子吗”?“可以”,光头答道。于是他们就口头拟定了建房的协议,定于甲寅年八月十五日丑时建造。 “什么坐南朝北,这些都是封建的东西”,他对着他的妻子说。村里密密麻麻的房子都是坐南朝北,先知们认为这是建房最好的朝向。于是他把定为坐西朝东,对着高耸的面前岭。“东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吉祥如意”,他自言自语道。日子依期而至。光头带着五个农民工来到了工地,挖地掏沙,忙忙乎乎地干了起来。光头则开着辆车到处乱逛。房子建在四处是槟榔树的一块地里,白天凉风习习的,夜晚则给人阴森感。离他家十米处有一户姓陈的人家,是一对刚分家出来的年轻夫妇,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凑齐了个好字。男的名叫陈文,异常好客,每每有客人到来,总是好酒美味款待。妻子阿兰虽说已生育,但仍貌美光艳可人。太阳西沉于罗牟山时,工人们常常聚在他家饮酒,谈些田野的什事。天气已渐凉,一些金黄的树叶散落在山间的小道上,踩上去沙沙作响。这是乡下人捕猎的时节。 太阳已渐渐升高,工人们在忙碌在砌着墙。一群小狗争抢着鸡骨头发出汪汪的狂吠声,臊臭的酒味随风散溢。脸红得发青的陈文举起酒杯对着他的同门说:“干”。俩人一饮而尽。“我们去新中买夹子怎样”?同门说。“好的”陈文应道。 同门那辆蓝色的雅玛哈在公路上疾驰着,一棵棵的道旁树木飞快地向后奔去,把小山遮掩得严严实实,只见那漫无边际的绿与天相接。一个小后,他们来到了三更罗镇境内的南平。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正在从公路的左侧横穿过对面去。“叭叭”,同门边按喇叭边加大油门冲了过去。老人并没有因为喇叭声而停了下来而是继续前行,或许是因为耳重的缘故。随着“砰”的一声巨响,老人被撞倒在路上;同门的牙齿七七八八地散落在路上,伴一点鲜红的血块,红白红白的,像一颗红宝石般耀眼;从摩托车的后座投出了一枝投枪似的身体,准确地投中了水泥路标上,重新把阿拉伯数字刷红了一番,血雨淋漓而下,像一朵盛开的红玫瑰,又像烟花似地飘落。 阿兰见到陈文时,他已被剃光了头,上面裹着一层又一层的纱布,脸色灰白地躺在急诊床上,药液正沿着小塑胶管慢慢地流进他的血管里。同门耷拉着脑袋、目光呆滞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张满是白布的床。“这是怎么回事啊,孩子他爹”?“快醒醒……都是我的错,我……”,同门站起来哽咽着说。“谁是病人的亲属?快签字,得赶快做手术……”。笔嚓嚓地在纸上写着,手术室的门砰地关上。十四点十分时,门终于被推开,一个身穿白大挂衣、头戴圆顶绿帽、口罩遮着嘴巴的医生出现在门口,双手无力地下垂,像树上吊着两个瓶子,在风中微微颤动。“医院吧,我们这边已无能为力”。口罩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划费处是三十多岁的女子在值班,一只白嫩的手飞速地按着计算器不断地发出“滴滴”的声音,她终于停了下来。打印机在“哧哧”地吞吐着,上面赫然闪现着一万七千三百二十三元。阿兰从裤袋里拿出了一把指甲钳,侧着身子,一条又一条的线被剪断了,露出了一个四指宽的口。她从里面掏出了一捆用黑色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的长方形的什物,是一叠纸钞。 在海口已一月有余,陈文的病情逐渐有了好转。阿兰想起了家里的小孩,于是她决定回家看看。槟榔树的影子渐渐地变长,那黑影逐渐吞噬了宇宙间的一点亮光。看到阿兰回来了,光头叫上他的一个工仔,提着一半烤鸡、两斤青菜和一箱啤酒往陈文家走去。“兰姐,文哥好点了吗?” “好点了,医院没回来”。 “哦” 光头应了一声就和他的工仔走进了厨房,把菜和那箱啤酒放在餐桌上,大大咧咧地坐在那红色的塑料椅子上。 “还没吃饭吧!” “还没哪” “先喝杯茶吧” 茶热腾腾的、冒出一缕缕的白气与那炊烟搅混在一起,从光头的脸上擦过,似乎也变得狰狞起来,目光不停地在阿兰的臀部移动。一滴水落在阿白的身上,惊得它汪汪地狂叫。 不久,菜都摆在了桌子上。光头从箱子里拿出了一瓶啤酒,用牙在瓶盖上一咬,“吱”的一声,瓶口吐出了许多白色的泡沫,顺着瓶口往下流到了桌子上,在桌面上形成了一滩水,然后嗒嗒地滴在了地上。 “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 阿兰拿起了一块抹布,走到了光头跟前,把桌子上的酒水慢慢地推至桌边。酒水刹时倾盆而下,如暴雨一般落在荒远的一角隅。一只咸猪手在桌子下晃了一下。光头不禁奸笑了一下,阿兰不禁颤了颤,似那刺骨的寒风一阵阵迎面吹来。酒瓶在桌子底下横七竖八地躺着,越堆越多。光头暗暗地盯了他的工仔一眼,露出了奸诈的光。 “方便一下” 工仔说罢就走了出去。外面,地上隐隐约约可见到草木躲在角隅里;天挂满了一闪一闪的星星。工仔踟踟踽踽地走到了其工地的宿舍,一头载了下去,不久就发出了呼呼的鼾声,弥漫着一屋的臭气。 “这家伙还挺聪明的” 光头暗自想到,就从那红色的塑料椅子上摔在地上。阿兰急忙走过去,低下身子,双手抓住光头的手使劲往上拉。光头的目光沿着阿兰的手往上看,一个凹字形的满是大雪铺盖的山谷呈现了出来。他急迫地扑了上去,紧紧地楼抱着大山。嘴里不断地喃喃着:“我爱你,我爱你……” (蒋明富)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uiniujiaoa.com/snjpzff/4441.html
- 上一篇文章: 活动回顾刚刚过去的河马生活节,我究竟
- 下一篇文章: 内心ldquo贫穷rdquo的4